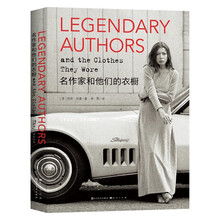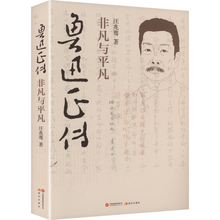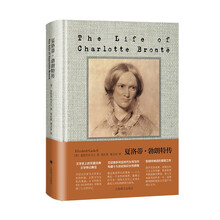①《云溪友议·艳阳词》有一段传说,录在这里作为补充,文云:“(元稹)自会稽拜尚书左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是时中门外构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传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乡国。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于是元稹有《赠柔之》相慰,裴淑也有《答微之》相诉(两诗参见文中所引)。这里应该注意:元稹大和三年九月奉诏启程入京,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虽然“留连”不去,“辞别”甚难,但也不至于直到年底才到京城。但是《云溪友议》所言,又与裴淑诗“穷冬到乡国”相合。我们以为其中是因为元稹在洛阳购买房屋,以供裴淑在洛阳生子,因而耽误了时日;我们还怀疑元稹自己从洛阳前往浙川田庄,作好自己退隐山林的准备。录此存疑,以待证之他日。<br>②这里《旧唐书·元稹传》“会宰相王播仓卒而卒”云云,《新唐书·元稹传》亦云:“王播卒,谋复辅政甚力,讫不遂。”我们以为此说不足为信,理由如次:第一,据《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四年正月十六日牛僧孺已入朝为相,而王播卒在其后的正月十九日,同月二十一日元稹已出镇武昌。从时间上来推测,似乎无此之可能。第二,据《旧唐书》的《李德裕传》、《牛僧孺传》、《李宗闵传》,牛僧孺入朝为相是李宗闵早就策划和一再援引的结果,而出贬元稹也是上年李宗闵勾结宦官排斥李德裕的继续。由此可知出贬元稹是李宗闽牛僧孺早就策划好了的,实与播仓促病卒无关。第三,元稹在长庆元年的考试事件中赞同复试,榜落李宗闵之婿苏巢,李宗闵也因此出贬为剑州刺史;元稹在相位又囚秉公召回李景俭等而与宰臣杜元颖等结怨。此时的元稹与正在相位的杜元颖、李宗闵、牛僧孺都有仇隙,连“左丞”之位都难于保住,清楚这一点的元稹又如何能“经营相位”?第四,何况元稹在尚书左丞位上“振举政纲,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之举又得罪了大大小小关系网内的人,树立了新的政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元稹倒霉势所必然,又怎能去“经营相位”?“经营相位”云云仅不过是政敌加在元稹头上的“莫须有”罪名罢了。<br>③卞孝萱《年谱》将《赛神》、《竞舟》两诗编入元和九年条下春天南行湘州之时。我们以为两诗云“年年十月暮”、“年年四五月”所述活动时间均与元稹元和九年春天为时短暂的湘州之行不合。《赛神》诗云:“我来歌此事,非独歌仁政。此事四邻有,亦欲闻四邻。”《竞舟》诗亦云:“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此州。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诗中的语气,不像是一个路经岳州的士曹参军的口气,而像是一个地方方面人员的口吻。元稹大和四年正月至五年七月任职武昌军节度使,分辖鄂、岳、蕲、黄、安、申六州,而岳州正在他的管辖区内。作为节度使,元稹有可能也应该视察过岳州,对岳州刺史的仁政加以赞扬,并以诗的形式要其他各州地方长官仿效。而他的任职武昌的时间,也完全涵盖了两诗中关于竞舟与赛神活动的时间。《年谱》同时将《茅舍》编入“庚寅至甲午在江陵府所作其他诗”栏下,我们以为《年谱》开头所引述的“前日洪州牧……斯人久云谢”,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此诗作年离开韦丹谢世的元和五年一定有相当的时间,应不在包含元和五年在内的元稹江陵任内。而且此诗开头“楚俗不理居”与《赛神》开头“楚俗不事事”、《竞舟》开头“楚俗不爱力”极为相似,应是同时之作。诗云:“我欲他郡长,三时务耕稼。农收次邑居,先室后台榭。”诗中的语气与《赛神》、《竞舟》一样像是一个地方方面人员的口吻,也应也是元稹武昌军节度使任内的作品。<br>④《年谱》将元稹的《洞庭湖》和《鹿角镇》诗系于元和九年。我们以为与《遭风二十韵》诗同为元稹武昌任内诗,理由是:一、《遭风二十韵》云:“洞庭弥漫接天回,一点君山似措杯。瞑色已笼秋竹树,夕阳犹带旧阳台。”这种洞庭湖秋天的大水景象与元和九年春天元稹拜见张正甫之行不合。又诗云“紫衣将校临船问,白马君侯傍柳来”也不是士曹参军而应是节度使才有的排场和威风,这证明元稹在武昌节度使任内曾到过洞庭湖地区。二、《鹿角镇》题注云:“洞庭湖中地名。”诗云:“去年湖水满。”这与《旧唐书·文宗纪》所云大和四年和五年鄂州岳州均有大水之记载相合。三、《洞庭湖》云:“驾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唯有君山下,狂风自古多。”所云都不是春天之景象,也与元稹元和九年春天湖南潭州之行诗所云不相符合。《鹿角镇》诗中所述“去年湖水满”等四句,也不合元稹元和九年春天拜访张正甫的情景;而且据《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八年除京师有水、旱、霜之灾外,鄂岳一带并无水灾的记录。而据《旧唐书·文宗纪》和《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大和四年与五年,鄂州都有大水,与“去年湖水满”相印证。因此我们认为,《洞庭湖)、《鹿角镇》、《遭风二十韵》都是元稹大和五年秋天巡视鄂州岳州时所作。其后不过数日,元稹即暴病谢世。<br>⑤《旧唐书》编撰者之所以如此贬低元稹的后期,我们以为原因之一即是轻信了裴度弹劾元稹的疏文。其中的《第一疏》,《旧唐书·裴度传》全文引录,可见编撰者对疏文的信从。在裴度的疏文中,元稹是“奸臣”和“凶徒”,所行的是“蔽惑聪明”、“挠败国政”、“恣行欺罔,干乱圣略”之事,编撰者焉能褒奖元稹后期所为?原因之二是受了冒名白居易而指责元稹的伪文《论请不用奸臣表》的欺骗。是文云“矫诈乱邪,实元稹之过”,“其事有实”;而对于元稹的“罪过”,“朝廷俱恶,卿士同怨”。既然元稹的朋友“白居易”所云都是如此,编撰者自然要否定元稹的后期了。《论奸》文北宋时被选入《文苑英华》,足见北宋及以前之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此文虽然后人已考出其为伪托,但那是以后的事。原因之三,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言元稹白居易“隙终”。孙光宪为唐五代时人,其时正是《旧唐书》编撰成书之年月。故孙氏所言代表了五代人的错觉,自然对编撰者也不无影响。<br>⑥宋代人宋祁与司马光在他们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之所以如此贬诽元稹,究其原因,元稹诗文至北宋时已散佚甚夥,已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详(元稹原有诗文集一百卷,至北宋刘麟整理时仅存六十卷即是明证)。宋祁司马光虽然不会看不到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元稹诗文,但他们对李唐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而致亡国的教训记忆犹新,故特别痛恨宦官与藩镇,进而仇视与宦官勾结反对平叛之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显然没有把元稹诗文和白居易韩愈等人对元稹评价加以认真研究、细致比较、科学鉴别,从而得出肯定元稹的结论;而是信从了《旧唐书》编撰者及裴度“白居易”等人有关元稹依附宦官破坏平叛的不根之言。将元稹涂抹得面目全非。这不仅是元稹个人的悲哀,也是李唐历史的悲哀。<br>⑦所述之事,见两《唐书》之《元稹传》所载。<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