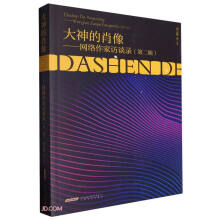有关奥运的个人记忆
与奥运结缘纯属偶然。
那是1993年的春天,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有一天接到通知去主持一场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举办的晚会,中英文都由我一个人来担当。我很认真地研究节目,不外京剧、杂技、武术之类国粹。中文好办,串词是现成的,但是直接翻译成英语是不行的。一是缺少背景介绍,老外恐不明就里,而且中文串词多慷慨激昂的对仗,翻成英语就显空洞,甚至莫名其妙。于是我决定英文干脆与中文脱离,另写一份,到时中英文穿插着说也不显重复。
当晚演出一切顺利。演出后,我正在后台卸妆,导演跑来说奥申委的几位领导要见我,其中就有何振梁先生。他一见面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评估团的官员都在说,这个中国女孩的英语怎么这么漂亮!你给咱们北京争了光!”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大概谦虚了一番。
不久就接二连三地主持一系列申奥活动,如萨马兰奇主席参加的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等等,直至七月份接到通知作为申奥代表团成员赴蒙特卡洛。我的任务很明确:一旦申奥成功,中国就要在当地举办答谢酒会,由我主持。虽然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英文专业,又主持了三年多以各国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正大综艺》,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从未去过西方国家,又是如此的大事,所以既兴奋也紧张。晚上睡不着觉,来回琢磨说什么话才显热情喜悦又不失大国风范,还专门定做了中、西式礼服各一套备用。出国的专机上,同我一样兴奋的团员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传着“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这回主办权肯定是咱的了!”
对另外一种可能性,我没有思想准备。
到了蒙特卡洛没几天,我的心中就有了不一样的预感。翻开每天的当地报纸,对北京的评价以负面为多。在整体政治气氛下,北京市官员的话被断章取义,一句“申奥不成,没脸去亚特兰大”就变成了第二天的大标语“北京如果申奥不成,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从哪儿说起呢?干着急,有劲儿使不上。同时,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复杂。我们的沟通能力与公关水平相比其他城市显得薄弱;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成天与自己人凑在一起。倒是合唱团的十二个女孩子在奥委会委员必经的走廊上唱《奥林匹克颂》,恳切又有点单薄。而悉尼的志愿者已经把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吧插满了他们的旗帜。中国的一些官员也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尖锐的问题时,竟然以“咱们会后再交换意见”作答。
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
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合唱团的女孩们抱在一起哭了,天真的她们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她们还唱得不够好。转播结束后,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从体育馆走回饭店。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雨后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水洼,路灯拖出我们长长的影子。回到房间,我把挂在衣橱里的礼服叠了起来,压进了箱子。那两件礼服,我从此再也没穿过。回国的飞机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输不起,而是因为何老特意走到我身边,说:“杨澜,真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都这个时候了,老人还想着我们,让我感动。透过舷窗俯视,美丽的蒙特卡洛阳光灿烂,白帆游弋,让中国人的失落如过眼云烟。我心里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怎么回来,我其实并不知道。
申奥的经历促使我做出人生的一个决定:辞去工作,出国留学。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那么少,对国际事务的认识那么幼稚,甚至,自己的英语那么不够用!
我要永远感谢2001年春节前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刚生了女儿两个多月,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呢,电话铃响了。是奥组委的赵卫,他自我介绍后就直接问:“我们想聘请你做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并且参加文化计划的陈述小组,你愿意吗?”“当然!”我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好像自己早就知道会接到这个电话。我只问,需要我什么时候到位?那天晚上,抱着怀里的孩子,我对她轻声说:“宝贝,看来妈妈要提前给你断奶了。对不起!妈妈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直到今天,女儿还会很骄傲地说:“妈妈,这么说我也为北京奥运会作过贡献是吗?”当然,宝贝!
2001年7月13日,当我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准备就北京申奥的文化计划进行陈述时,我一点都不紧张,甚至不去想最后的结果。邓亚萍事先对我说:“想赢就不紧张,怕输才紧张。”而我的心得是:“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我的使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些凝聚了多少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我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结尾处我说:“七百年前,当马可·波罗即将去世时,人们再一次问他:‘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东方中国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可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发现中国。”这些话打动了他们,我深信不疑。
也许这样说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我还是认为,1993年申奥失利未见得不是好事。只差两票,挺“冤”的,也不“冤”。就像任何一场体育比赛,有本事就别差那0.01秒。输,就要认。有些事必须水到渠成,瓜即使强扭下来,也是不甜的。中国人当年有点心急,急着出头,急着证明给人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心不急,也发展不了这么快。但高楼大厦起得容易,改变理念、提升管理能力和民众的文明素质就没那么容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全体眼巴巴地盼着运动员拿一块金牌为国争光,因为那时咱们觉得处处不如人,需要金牌长志气。结果,运动员们不堪重负,奥运金牌也改变了味道。朱建华在汉城一失利,上海家里的玻璃就被砸了;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下飞机时就要老老实实走在最后一个。走在第一位的高敏吓得脊梁发冷,得到的鲜花越多,越怕承担不了日后的失败,不惜装病也要闹着退役。这让她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精神考验。那时的中国人,输不起啊。
而今天,我们可以接受因伤退赛的刘翔,能够为郎平指导的美国队喝彩。尊重一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把集体的意志强加于人,这就是中国的进步。人有了底气,眼光就会放远些,心胸就会宽阔些。就像你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人家问你为什么,你是说“因为想秀一秀家里的新装修”,还是说“因为想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有了这种心态的成熟,目标也就更单纯些,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民族在成长中必然经历的烦恼,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去面对。
从两次申奥至今,我有幸参与了诸多奥运活动:奥运金牌的发布、倒计时一周年、倒计时一百天、火炬接力、残奥圣火采集、奥运歌曲的评选,等等。
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我告诉他们说:“主办奥运不仅是政府的意愿,更是中国民众的意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从此都将大不相同。以往对彼此刻板的印象将被一张生动的面庞取代。生逢其时、与之同行,是多么幸运的事。”当我告诉国际媒体,北京奥运需要十万志愿者,却有二百万人报名;北京的公共场所已禁止吸烟;公共厕所全面整改,低排放绿色交通工具在奥运会期间使用,日后将在十个超大型城市中普及推广,大幅降低废气污染……他们都睁大眼睛说:“我们怎么不知道?”有些固有观念的确会遮蔽视野,那是有选择的盲点,连当事人也不一定意识到。西方人往往不了解,从“东亚病夫”的称呼到刘长春只身赴洛杉矶奥运会,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女排夺冠到许海峰的第一枚奥运金牌,这一切对于中华民族挣脱屈辱,争取复兴的历史意义。而很多中国人往往把奥运当作盛典而非“派对”,显得庄重有余而轻松不足。对于西方人而言,派对就要热闹,甚至有点乱,各种人都来露露脸,闹点动静。东西方的观念沟通,还需要时间。但奥运让我们看到了这距离正在缩短。在主持奥运会开闭幕式前暖场演出的时候,我们带领全场观众用双手做出白鸽飞翔的姿势,又在主火炬熄灭时打开手电显示每个人心中不灭的火焰,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场。对和平与美好的祝愿不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吗?
在奥运年,《杨澜访谈录》改变以往的周播形态,制作50集系列采访,在东方卫视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访了国内外50位奥运人物,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山铺路的优秀组织者,有奥运史上伟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本届奥运会上的风云人物。奥运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宏大叙事,也是冷暖自知的个人体验。
参与奥运,不必非要有一个崇高的理由,但它确有一种能量把人带向更高处。
对于都灵冬奥会男子单人花样滑冰冠军普鲁申科来说,滑冰是母亲为了让瘦弱的儿子变得强壮。11岁那年,家乡的滑冰场关闭了。普鲁申科只身来到圣彼得堡投靠教练。为了负担儿子的费用,父母不得不打几份工,母亲一度在马路上干铺沥青的重体力活。形单影只的普鲁申科不仅饱一顿饿一顿,而且屡屡遭受同队大男孩的欺负。好几次他在火车站目送母亲离去,不由自主地跟着火车奔跑,呼喊着妈妈把他一起带走。但他终于坚持了下来,滑冰是他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今天的普鲁申科已经把该得的奖杯都拿了,是什么让他在都灵退役之后又宣布了参加2010年的冬奥会?“我要创造历史,因为还没有人能连续两次拿到这个单项的奥运金牌。如果去做职业滑冰选手,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不,我的目标是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成为伟大的运动员,也是23岁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的追求。他毫不讳言速度对他的诱惑,也不掩饰对胜利的渴望。打破1972年在慕尼黑由马克·史皮茨创造的一届奥运会独得7枚金牌的纪录,恰恰是这一不可能的任务让他激情四射。年轻就该好胜。他所向披靡地摘下400米个人混合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200米自由泳、200米蝶泳、4×200米自由泳接力、200米个人混合泳、100米蝶泳、4×100米混合泳接力8枚金牌,并在水立方中创下了七项世界纪录!这位连圣诞节都不曾停止训练,把竞争对手的照片贴在床头的年轻人,大声告诉世界:追求卓越就要不遗余力。当他兴高采烈地奔向看台上的母亲和姐姐,一次次拥抱她们的时候,他又完全像个大男孩,希望得到妈妈的赞扬与宠爱。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自己只要离开水面,就会笨手笨脚地弄伤自己,今天跌断了手腕,明天崴了脚踝。但只要一跃入池,他就像鱼儿回到水中,自由自在,舒展畅快。水是他的世界。我们只有揉揉眼睛,相信这一切绝非梦幻,并为能够亲眼目睹伟大的菲尔普斯追风破浪、创造历史而深感荣幸。他代表的不仅是美国队,他代表的是我们人类。
时间是多么无情,在它面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相隔实在过于漫长;时间又是多么有情,它让精彩成为经典,瞬间成为永恒。当巴德·格林斯潘陪同杰西·欧文斯重返柏林,这位黑人运动员1936年打败希特勒种族优越论的奔跑声依然震耳欲聋。一位普通的德国人对他说:“当年希特勒不肯与你握手,现在请允许我握一握你的手吧。”在那一刻,格林斯潘决定用他一生的时间来记录奥运会上一个个人性闪耀的时刻。“我采用的是海明威武的讲述方式。简单的叙事,人,命运,不屈的精神。”正是他,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把摄影机对准了马拉松赛的最后一名选手,来自坦桑尼亚的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这是一位来自非洲的一个小村庄,习惯了赤脚跑着上学的年轻人,代表刚刚独立不久的祖国来到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高海拔让他难以适应,跑到一半的时候就扭伤了大腿。一个又一个选手超过了他,救护车就在一边,招呼他上去。他拒绝了。天黑了,体育馆内颁奖仪式已经结束,看台上已有不少观众离去了。就在这时,阿赫瓦里一瘸一拐地跑了进来,在冲过终点时颓然倒地。记者问他为何明知是最后一名还要坚持跑完。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我的祖国把我送到7000英里之外,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为了完成比赛。”2007年我的节目组通过坦桑尼亚驻华使馆找到了已近七旬的阿赫瓦里。他居住的村庄至今没有通电,离他最近的一部电话和电视也有两公里的路程。作为老年人和学生的业余教练,他没有太多的收入,但他很骄傲,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祖国丢脸,并且成功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仍然坚持每天跑步,这已是一种生活方式。
阿赫瓦里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虽败犹荣”。而埃蒙斯夫妇告诉我们的是,对待比赛的结果,我们也不必太过认真。
2008年8月19日,当得知来自美国和捷克的埃蒙斯夫妇将接受采访时,我已梳理好故事的脉络:男主角马修四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三姿步枪的比赛中以大比分领先,眼看金牌就要到手,却在最后一射时鬼使神差地打错了靶,把冠军拱手相让于中国的贾占波;但祸兮福兮,他结识了前来安慰他的捷克女射手卡特琳娜,并喜结连理。这次夫妻双双赴会,已获一金两银的佳绩,就差马修的一块金牌了。同样是在步枪的三姿比赛中,同样是在一路领先的情况下,马修在最后一枪竟然失误只得到4.4环,重演雅典悲剧。这次得到金牌的是另一位中国选手——邱健。这真是命运的捉弄!我提醒自己,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让夫妇俩感觉太糟。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他们竟然如此快乐、甜蜜、满足,充满幽默感,真是大大出乎意料。“这是上帝的一个玩笑吧,一定会有一个理由。”他们自我调侃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天哪,如果说上次的理由是让他遇到她,这次还能是什么?“也许如果他这次得到冠军,就可能会放弃射击了,但现在你猜怎么样,他还会继续努力,为201 2年奥运会奋斗。”妻子拉着丈夫的手说。他们认为比金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运动员长期的表现,以及在赛场上对输赢表现出来的风度与品格。对于他们来说,在比赛结束后向获胜的运动员真诚祝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同样笑着与赛场挥别的还有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王楠。在获得女子团体金牌之后,她以一枚单打银牌正式退役。她的脸上没有遗憾,只有灿烂的笑容。她说:“四年前,当有人提出让我参加2008年奥运会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时我就30岁了,这怎么可能?”经历过悉尼奥运会的辉煌和釜山亚运会的惨败,她需要的不是用多一枚的金牌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完成对生命的一次超越。2006年,被诊断出甲状腺肿瘤的王楠度过了艰难的时刻。新婚不久的丈夫每日守护,给了她强大的情感支撑。“有一次他跟我妈急了,因为她说早知道楠楠这样,你们再晚点领证好了。”今天的王楠不愿渲染当初的病情,但对这一段患难真情却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她同样不会忘记,在她比赛失意的时候,由爱人送到赛场的一万零一朵玫瑰。这寓意“万里挑一”的甜蜜让她知足、幸福,虽然她嘴上也会故作责怪地说:“全国十几亿人,怎么只是万里挑一呢?!”难道要让人家种玫瑰不成!北京奥运会女乒单打决赛结束时,王楠第一个跑向看台上的丈夫,享受老公的一句:“你打得很精彩,太棒了!”此时的王楠还复何求?她怎么能不笑呢?
运动,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Game,是竞赛,也是游戏。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孩子们因为希望有朝一日像迈克尔·乔丹一样打篮球而对毒品说“不”;饱受战争摧残的塞黑青年可以在废墟间的空场上踢一场足球,暂时忘记苦难与悲伤;受宗教保守势力束缚的中东女性,正在鼓励她们的女儿们穿上运动服参加运动。奥林匹克,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让人们在人性的原点上彼此接近。当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获得200米金牌并再次突破世界纪录时,鸟巢中九万多观众齐声高唱“生日快乐”,第二天,他就宣布为四川灾区的孩子们捐款五万美金。怪不得,奥运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由衷地感叹说:“无论一个导演怎样伟大,都不可能导演出这样具有震撼力的戏剧。运动员才是奥运会真正的主角,在他们面前,一切创意都显得微不足道。”
汶川大地震与奥运发生在同一年,使2008年更加不同寻常。自然的威力让人敬畏,生命的损失让人痛苦,活着的人相互扶助守望,让中华之精神在瓦砾中获得新生。当经历风风雨雨的奥运圣火穿越废墟,在生存者的手中,在英雄的手中,在孩子的手中,在祖祖辈辈以此为家的人们的手中传递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热泪盈眶。少了炫耀浮躁之心,有一种更深沉的情感托起奥运的火焰:回到文明的起点,感受生命的尊严与顽强,人性的美好与高贵。我们在奔跑,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会继续奔跑,因为没有对未来失去希望。血液在身体里加速流动,四肢舒展开来,神经变得兴奋,奔跑带来的快感如此单纯而直接。当人们手手相传、心心相连的时候,我们同时拥有了一种大于个体自身的力量,这正是人类精神不断自我超越的写照。
在这个冲突、饥荒、环境危机不绝于耳,误解、偏见与仇恨分割着人群的时代,有什么力量让我们作为人类聚合在一起?人道的力量。有哪种人道的力量让人充满身心的喜悦,发于本性,彼此相通?运动的力量。有哪个运动会吸引了世界上最多的国家运动员,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竞技水平?奥林匹克运动会。
与奥运结缘,绝非偶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