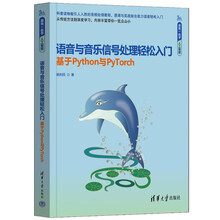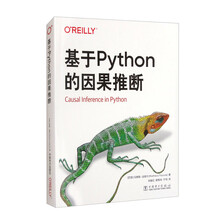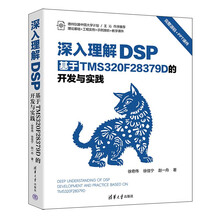第一章 生活的激情<br>五百年前的古人而言,历史事件的轮廓比现在看上去要清晰得多。对他们而言,欢乐与悲痛、好运和厄运似乎比今人感觉到的更加分明。每一种经历都更加直接和绝对,人们对悲欢的感觉很像是儿童的感觉。每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行为举止都是用给定而明确的形式界定的,都符合组织严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该有的庄重精神。由于基督教的圣事,人生的大事比如生老病死都沐浴在神秘的光辉之中。不过,即使是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出行、劳作和探亲访友也必然在祝福、仪式、格言和惯例的环境里发生。<br>对那时的人而言,缓减不幸和疾病的手段比较少,所以灾害和疾病比现在可怕,更令人痛苦。疾病和健康的反差更加强烈。刺骨的寒冷和漫长的冬夜更加可怕。对荣誉和财富的欣赏更加狂热而贪婪,因为它们与令人悲叹的贫困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暖和的皮袄、明亮的炉火、说笑中的畅饮、柔软的卧榻都是高尚的人生享受,这种惬意的感觉恐怕比英格兰小说长期热衷的描写还要更加悠久。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看上去都更加明晰,更加无情地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麻风病人摇晃着警铃走路,公开展示他们身上的残疾。每一个人的等级、教阶和职业从衣着上都一望而知。达官显贵无不招摇过市,出门总是佩带武器,总有穿制服的仆人跟随,使人不由得不敬畏和嫉妒。司法的执行、商品的销售、婚礼与葬礼都是在喧哗中进行,都伴有队伍的行进、高声的喧闹、悲痛的哀号和嘈杂的音乐。2男人佩戴情人的标记,兄弟会的成员佩戴兄弟会的徽号,仆人都携带主人的旗幡和纹徽。<br>从外观上看,城市和乡村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差和色彩。那时的城市不像现在的城市,不会到处可见相貌粗糙而丑陋的工厂、单调乏味的住宅,而是城墙环绕,画面圆润,难以计数的尖塔直指蓝天。贵族和商人的高大豪宅,用沉甸甸的石头修建,但无论其公馆多么宏伟,巍峨的教堂还是傲视各种建筑、主宰着城市的景观。<br>那时的冬夏差别比现在强烈,白昼与黑夜、安静与嘈杂的反差同样强烈。现代都市不知漆黑的夜晚为何物,也无法体会真正的万籁俱寂,亦不能体会一盏孤灯的昏暗,更不能察觉远方传来的孤零零的人声。万千气象以连续不断的反差和色彩斑斓的形态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头脑,日常生活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富有激情的暗示,显示大起大落的情绪,不加修饰的热情、突发的残忍和温柔的情感,中世纪城市的生活就是停留在这样的氛围中。<br>然而,在中世纪嘈杂的繁忙生活中,有一个声音总是压倒一切的,这就是钟声。无论大小,钟声都绝不会与其他声音混淆不清。有一阵子,钟声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提升到井然有序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钟声就像关怀人的、善良的精灵,总是以熟悉的声音宣告悲伤或喜悦、平静或焦躁、集会或告诫。人们熟悉各种各样的钟声,赋予它们亲切的名字:肥胖的雅克琳(Fat Jacqueline)、贝尔?罗朗(Bell Roelant),人人都熟悉它们的音调,并能够立即分辨出它们不同的意义。无论这些钟声使用得多么频繁,人们对这些钟声都不会失去兴趣。1455年,瓦朗谢纳瓦朗谢纳(Valenciennes),法国北部城市。城内两帮人臭名昭著的对决使全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使勃艮第宫廷也感到紧张。在对决的过程中,钟声一直响个不停。史家夏特兰云:“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把警报的钟声称为“恐怖的钟声”,“作恶的钟声”。新的教皇当选、教派纷争停息的时候,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阿马尼亚克(Armagnac),法国西南部地区,历史地名。和解的时候,3巴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钟都被敲响了,整天整夜响个不停,那钟声实在是震耳欲聋。<br>频繁的游行亦扣人心弦。在时势艰难时,游行十分频繁,有时天天游行,连续几个星期。1412年,奥尔良王朝和勃艮第王朝的致命冲突最终导致公开的内战,法王查理六世举起皇家的旗帜,和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John the Fearless)联手打击阿马尼亚克人,因为他们和英格兰结盟,背叛了法兰西。只要查理六世还在异国的土地上作战,巴黎人都会接到命令天天游行。这一次的游行从五月一直持续到七月,每次的游行总是有不同的社会团体、教派、行会参加,总是有不同的线路,总是用不同的圣物,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最扣人心弦的游行”。所有的人都打着赤脚,空着肚子,议员和穷人无异;凡是有财力的人都手捧蜡烛,高举火把。许多儿童也加入游行者的行列。连巴黎周围乡村的穷人也赶来游行,他们也打着赤脚,急急忙忙奔跑进城。游行的也好,旁观的也好,人人无不为之动容,“人们呼天抢地,挥泪如雨,洋溢着无尽的虔诚”。在游行的这三个月里,大雨一直下个不停。<br>还有王侯参与的盛大游行,由阵容强大的演员表演丰富多样的节目。另一种场面是终年不断、频频举行的行刑仪式。行刑的面具有着可怕的吸引力,激发起本能的同情心,成为人们精神营养的重要成分。为了惩治凶恶的抢劫犯和杀人犯,法庭发明了可怕的刑罚:在布鲁塞尔,一位年轻的纵火犯和杀人犯被处以极刑时,用铁链把他锁在一根柱子上,柱子上捆着熊熊燃烧的干柴,他被大火逼得围绕火刑柱转圈奔跑。临刑前他自我介绍,现身说法,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他的话“打动人心,令人落泪,人们称赞他这种从未见过的从容赴死”。在勃艮第人统治巴黎的恐怖时期,一位名叫曼沙特?迪?波伊(Nansart du Bois)的贵人被送上断头台。4他是阿马尼亚克人。刽子手按惯例请求死囚原谅,他不仅原谅了刽子手,而且请刽子手亲吻他。“刑场上围观者众,观者无不热泪盈眶。”<br>被处死的牺牲品常常是地位显赫的王公。此时目睹这样严厉的刑罚,人们会更加满意,高贵者尊位难保,这给世人的告诫更加严厉。亲眼目睹这样的极刑比看画面上的极刑更加令人震撼,比看死亡舞蹈更加令人恐惧。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模拟人走向死亡的舞蹈,常戴面具,常见于诗歌。又见本书第五章。——英译者注行刑当局费尽心机,务求给观者留下的印象没有欠缺。这些贵人走向刑场的装饰是他们地位的象征。宫廷总管让?德?蒙太古(Jean de Montaigu)由于遭惹无畏者约翰的仇恨而被处死,他从容地登上架在一辆马车上的绞刑架。两位鼓手为他开道。他着装富丽堂皇,礼袍、礼帽、背心、长裤一应俱全,长裤红白相间,皮靴上套着金马刺。被处决之后,尸体吊在绞架上示众,但他脚上的金马刺仍然闪闪发光。1416年,富有的教士尼古拉?德?奥热蒙(Nicholas dOrgemont)成为阿马尼亚克人家族仇恨的牺牲品。他被囚禁在一辆垃圾车上,在巴黎街头示众,但被允许身穿紫色长袍,头戴紫色礼帽,示众的同时要他旁观他的两位同伴被处死,示众以后他被投入大牢终身监禁:“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以赛亚书》30:20)。乌达?德?比西(Oudart de Bussy)由于拒绝接受议会里安排的席位而被处死以后,路易十一又命令开棺暴尸羞辱,即使这样,还是允许他头戴猩红色的皮毛头巾,以“符合议员着装的风格”。他在赫斯丹镇暴尸时,布告辞是一首诗。路易十一用无情的幽默记述了这桩案子。<br>除了游行和行刑之外,还有云游僧的布道,这样的事情相对比较少见,却也时有发生。他们的布道辞使人激动不已。我们今天的读报人很难想象,口头的布道对淳朴的目不识丁的头脑能够产生多么大的冲击力。很受欢迎的修士理查德可能曾经倾听过圣女贞德圣女贞德(Joan of Arc,1412-1431),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时率军六百解除英军对奥尔良城的围困,后被俘,并被火刑处死。的忏悔。1429年,他在巴黎连续布道十天,从早上五点讲到十点或十一点,5地点是在圣童墓园。那里有一幅巨型的死亡之舞壁画,他背向骷髅室的墙壁讲话,室内穹窿形走道的两边堆满死者的颅骨。第十天布道结束时,他告诉听众这是他最后一次布道,因为他没有被获准继续布道。“无论地位高低,听众都打心眼里感到难过,他们都失声痛哭,仿佛他们最知心的朋友即将下葬,理查德也禁不住放声痛哭。”他离开巴黎以后,人们仍然相信,下一个礼拜天他会回到圣丹尼教堂布道。根据《巴黎市民报》记载,大约有六百人之众在星期六晚上就出城去守候,他们在田野里过夜,以便占据最佳的座位第二天听讲。<br>同样,方济各会修道士安托万?符拉丹(Antoine Fradin)也被禁止在巴黎布道,因为他抨击政府的弊端。然而,这正是他受人民爱戴的原因。人们在科尔德利修道院保护他,昼夜为他站岗放哨,妇女们用烟灰和石头做武器准备战斗。人民嘲笑禁止站岗的命令说:“国王不知道我们在站岗!”最后禁令被强制执行时,符拉丹被迫离开巴黎,人们出门给他送行,“呼天抢地,哭声震天”让?尤维纳尔著《编年史》,Chron. scand., II, p. 70, 72。——原注。<br>多明我会修道士文森特?费雷尔(Vincent Ferrer)云游布道。在他所到的大大小小城镇,往往都万人空巷,喜迎他的到来,平民、行政官员、神职人员包括主教和高级教士都倾城而出,高唱赞歌。许多支持者随行云游,每天日落之后,拥戴他的人都组织游行,用鞭笞表现圣徒受难,载歌载舞。每到一座城镇,都有新的拥戴者加入他的行列。他雇用名声清白的人负责给养,仔细安排随行人员的吃喝和住宿。不同教派的牧师随行协助他倾听教徒忏悔,主持弥撒。一些著名的司法界人士随行记录他调停的案子,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设法使人和解妥协。当他布道时,随行人员总是用木栅把他围在中间,确保他的安全,6因为成群的听众拥挤着要亲吻他的手或道袍。每当他布道的时候,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在场听众无不感动落泪。当他讲到末日审判、地域的痛苦或耶稣受难时,他和听众都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以至他不得不稍停片刻,待哭泣声停歇。忏悔者在听众面前双膝下跪,哭诉自己的罪孽。在1485年大斋节,著名的奥利维埃?马亚尔(Olivier Maillard)牧师在奥尔良布道时,许多人爬到房顶上去听讲而造成房屋的损毁,事后的修缮工作竟然花去了六十四天。<br>这一切都类似英格兰—美利坚复兴的氛围或救世军的氛围,但它的影响在社会各方面无孔不入,公开暴露的程度也高得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费雷尔的影响是传记作家的夸张。另一位态度冷静、语气单调的传记作家描写一位叫托马斯的修道士时,表现出几乎完全相同的风格,这位作家名叫昂格朗?蒙斯特雷(Enguerrend de Monstrelet)。1498年,这位自称加尔默罗会修士的托马斯在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布道,也掀起了一阵旋风——不过后来发现他是假冒的修士。地方官也出城迎接他,贵族为他的毛驴牵缰绳,许多人包括贵族乐意离别家庭和仆人去追随他四处云游,传记作家蒙斯特雷还指名道姓地谈到其中一些贵族。地位显赫的市民为他筑起高大的讲坛,用最昂贵的挂毯装点他的布道坛。<br>除了耶稣受难和人生临终四要事(死亡、审判、天国和地狱)之外,这位受欢迎的托马斯修士布道时还抨击奢侈和虚荣,这样的抨击也使人落泪。据蒙斯特雷记述,人们特别感激托马斯神父,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抨击炫耀和虚荣,尤其抨击贵族和教士。他喜欢怂恿小童(据蒙斯特雷记述,他许诺给小童赎罪券)去纠缠那些贵妇人,看见那些敢于戴高耸头巾的贵妇人时,小童就高呼:“帽子!帽子!”于是,在托马斯布道期间,贵妇人再也不敢戴这种高帽,她们像修女一样戴头巾。这位忠实的史家说:“此间,她们就像蜗牛,有人走近时把触角缩进去,没听见人讥讽时又把触角伸出来。7托马斯离开后,她们迅速复旧,我行我素,而且她们的头饰比原来还要更加精致、更加高大。”<br>托马斯修士和理查德修士点燃了火葬虚荣的干柴。1497年,接踵而至的佛罗伦萨烈火形成燎原之势,史无前例。萨沃那洛拉萨沃那洛拉 (Girolamo,1452-1498),意大利宗教和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教廷和暴政,发动佛罗伦萨起义,建立民主政权,被教皇推翻、逐出教会并被处死。煽动起义,造成无可挽回的艺术损失。之前的1428年和1429年,巴黎和阿图瓦爆发的骚乱仅仅局限于焚毁纸牌、牌桌、骰子、头饰和小玩意,而且是男男女女自愿交出的玩意。在15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这一类火葬常常是布道者煽起的虔诚宗教情绪的表现。忏悔者悔恨虚荣和贪婪的感情在仪式中被体现出来,真诚的虔敬在庄严的集体行动中以程式固定下来,因为那个时代的倾向是使一切东西程式化。<br>我们得换位思考,才能够理解当时的人为何思想上容易受影响,才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容易感动落泪,容易忏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评判,那时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多姿多彩,他们的情绪是多么的强烈。<br>公众哀悼的场面似乎是对灾祸的真诚反应。在查理七世的葬礼期间,人们看见送葬的队伍临近时,往往会悲痛得不能自已:所有的宫廷官员“身穿丧服,官员们哀悼国王,悲痛万分,涕泪滂沱,观者亦深感悲痛,全城的哀叹声不绝于耳”。国王的六位近侍骑马行进,马身上披着黑色的天鹅绒以示哀悼:“天知道这些马多么悲伤,多么想表达自己的感情,它们也要哀悼国王啊。”一位近侍悲痛难忍,四天滴水未进,饮食难咽。人们动情地诉说自己的哀伤。<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