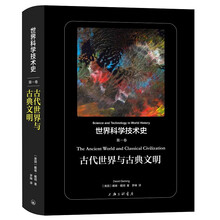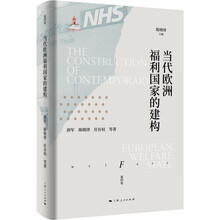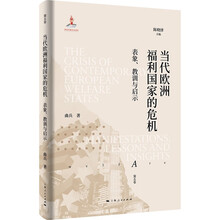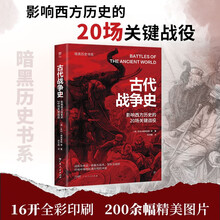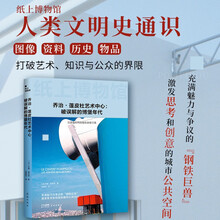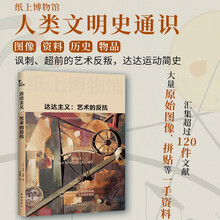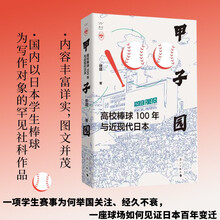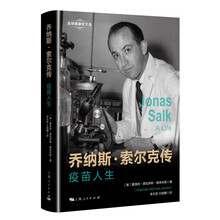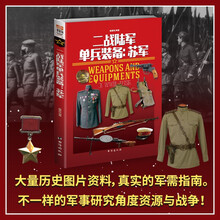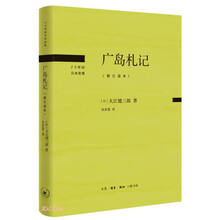第二节 引进和推动“中国热”
17世纪对于俄国汉学来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这时俄国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形成,它向西和向南推进,企图打通出海口。为了向东寻求扩张的陆上通道,便开始注意中国。俄国重在了解中国的地理交通与政治经济情况,以便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探索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的可能。所以在两国的联系中,此时的俄困处处表现得很主动。这也是其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促成的。
据史籍记载,约在明末清初之际,俄国官方开始设法获得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17世纪初叶,1618年(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伊凡??裴特林奉托波尔斯克督军之命出使北京,回国后于1619年写了《中国一览》。1654-1657年(清朝顺治十一年至十四年)费奥多尔??裴可甫出使清廷之后写了《中国实录》。二十年以后,另一个俄国使团由尼古拉??斯帕法里率团于1675-1678年进驻北京。这位外交官写出了俄国最早描述中国问题的著作《中国漫记》。其所著的《1675-1678年尼??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经尤??瓦??阿尔谢尼耶夫整理)后于1906年出版。随着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国派出第一个商队来华进行贸易。此后,两国之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的来往也日益发展,双方都有了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需要,便开始了培养人才的工作。
此外,俄国官方为了加速人才培养工作和加强对中国的了解,还从西方引进了汉学人才。彼得大帝1724年下谕旨成立帝国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并聘请德国东方学家拜耶尔任科学院院士,旨在协助俄国引进西欧汉学的成果。拜耶尔本人就是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的作者。彼得大帝的继任人又派出了一些在俄国宫廷任职的外国人出使中国。如1730年派瑞典人洛伦茨??郎喀出使中国,为俄国科学院获得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图书,那就是俄国汉满文图书馆的基础。其他被派出使中国的还有荷兰人伊兹勃兰德??伊德司、丹麦人亚当??勃兰
特、苏格兰人约翰??贝尔等。他们也都分别留有文字记录,但那些文章、著述似应分属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汉学。
俄国汉学酝酿时期的另一种形式是引入“中国热”。“中围热”也称“中华风”,是一种对中国社会风气的“迷恋”,兴起于17世纪未18世纪初的西欧。那时中国与西欧已建立了海上交通,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德等国的知识界推崇中国文化,宫廷和上层社会热衷于收藏中国文物,甚至仿建中围式样和风格的庭园。这些都引起了俄国人的注意。于是俄同人在“全盘西化”(彼得大帝改革)、全盘学习西欧的同时,把西欧盛行的“中国热”也引了过去。
俄国早期兴起的“中国热”,除了法国和西欧各国“中国热”的促进之外,还有就是俄国东正教宗教使团从1715年定期派驻北京,经常传达回去的信息。
18世纪从法国兴起并遍及欧洲的“中国热”,对俄国有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赞叹中国完美道德的文章、宣扬孔子教义的著作以及他取材于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而编成的剧作《中国孤儿》,曾经影响了俄国文坛的风气。1788年涅恰耶夫把伏尔泰所著该剧译成俄文。此前,1759年剧作家苏马罗科夫就从德文译出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作家拉吉舍夫在西伯利亚写了《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札》,诗人康杰米尔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诗人杰尔查文的诗中一再提到中国文化。此外,剧作家冯维辛从德文翻译了儒典《大学》。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两家杂志相继刊登了宣扬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一篇是1770年2月《雄蜂》登载的《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宋朝程颐《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的摘译),一篇是1770年7月杂志《爱说闲话的人》上登载的《雍正帝传子遗诏》。
在俄国沙皇中,对“中国热”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先后在位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其女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1年执政)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62-1796年执政)。
彼得大帝特别关注中国文化,而在他之后的两位女皇——伊丽莎白和叶卡捷林娜二世,更显示出对异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分别引进了国外的文物和文化思潮,并且着意于推进中国热潮。前者因营造中国环境、中国氛围而获得“伊丽莎白的中国格调”的称赞;后者以宣扬中国皇帝、提倡中国古代文明而著称。
传人俄罗斯的中国文化,不仅范闱广,而且种类多,有典籍,也有实物。典籍包括各类文学作品,以及哲学、宗教、历史、法律、经济、民族 、艺术等领域的种种著述;实物则包括艺术制品和珍奇古玩,从建筑、装饰.到民间年画、剪纸、日常摆设,甚至出土珍品、养生挂图等等,无所不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