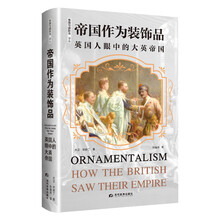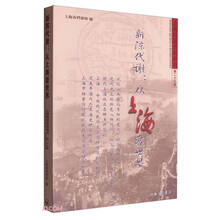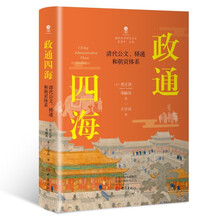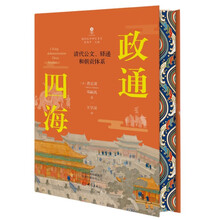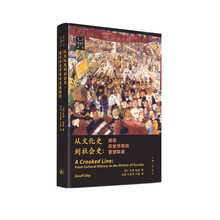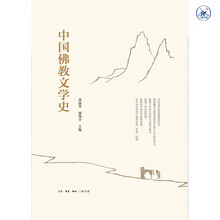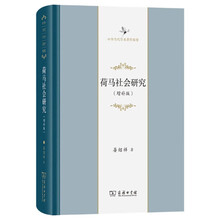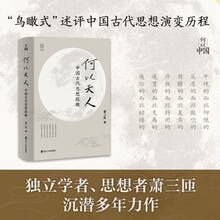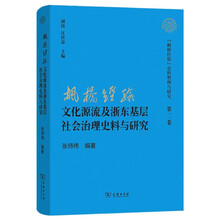昆仑奴考
西历一八六三年,在中国的民族革命的首领洪秀全定都金陵下令放奴婢禁娼妾(一八五三)之后的十年,美国大总统阿拉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公布释奴令。在这中间,从一八六○到一八六五的六年中,美国的南北部发生了一场极激烈的释奴战争。
这场为解放黑奴(Negroes)而起的战争,结果是解放了几千万的黑色人种,从高压的残酷的待遇下给还了他们的身体的自由,生命的保障。在历史上也表明了它的光荣的意义。
不过就反面看,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连绵六七年,流血数百万的可怕的战争,才使我们知道解放黑奴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这件事是付了如此一笔巨大的代价才完成的。再进一步看,是因为有了一本著名的暴露黑奴惨无人道生活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出现而引起世人一致的注意,而努力于解放黑奴运动而引起这次为人道为正义的战争。
在阿拉伯人的土耳其人的著名的中世纪故事《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上,我们时常看见有不识不知的黑奴在服侍着他的养尊处优的主人。在许多的十字军故事(Crusades Story)上,我们也时常看有无数的黑奴在为他的主人——武士荷刀执盾。在无量数的诗歌、故事、神话上,无论是西班牙人的,英国人的,土耳其人的,我们也不时看见有黑奴在劳动着的事实。
因此,这些无量数的关于黑奴的叙述,使我们的脑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对黑奴的整个的生活的概念,同时也引起了一个黑奴制度是欧美非洲人的历史上专有的一个制度,一件事实。
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固定,从许多不完全的零章断旬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在中国,在林肯发布释令以前的一千二百年,在六世纪或更前的时候,中国已有黑奴制度的存在。
以下我要叙述的是六世纪以来的中国黑奴的史实,中国黑奴的来路,中国黑奴的特点与技术,及其关于黑奴的史料。
一
昆仑奴最早见于文献的怕是《隋书·陈棱传》与《隋书·四夷传》中的《琉球国传》。《通志》卷一百九十四《四夷传·琉球》条说:
初(陈)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喻降之,琉球不听。
《文献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第二页“琉球”条所载与此同。再看《隋书·四夷传·琉球》条:
大业三年(六○七)遣朱宽入海至琉球,明年复往,使陈棱击之。
陈棱击琉求是西元六。八年的事,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昆仑人是在这时期已经有在中国服军役或竟是奴隶的了。
昆仑山是一个岛名,在东京湾中,近安南南部海岸。《南史》说:“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旧唐书·林邑国传》也说:“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昆仑有军屯山、军突弄山、昆仑国、昆吨山诸异名。晋张华《博物志》水门,采吴自牧《梦梁录·江船海舰》条,宋赵汝适《诸蕃志·阇婆国》条,《宋史·外国传·阇婆国》条,《文献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阇婆》,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昆仑》条,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费信《星槎胜览·昆仑山》条,《四夷·馆考》下《暹罗馆》,黄衷《海语》卷三《昆仑山》,清胡学峰《海国杂记·大昆仑》,都有大同小异的关于昆仑之记载,今略举三书列之如下:
“冷海半月,至昆仑国。”——《宋史·外国传·闽婆国》条。按《文献通考》所载与此同。《酉阳杂组》亦有《昆仑国》。
“其山节然于瀛海之间,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根盘旷远海之名曰昆仑。凡往西洋商贩,必得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按宋吴自牧《梦梁录》作‘去怕七州,回怕昆仑’——此山产无异物,人无居室,而食山果鱼虾,居树巢而已。”——罗振玉影印本《星槎胜览》
“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于瀛海中,与占城、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有男人数十人,怪形而异状,穴居而野处。即无衣褐,日食山果鱼虾,夜则宿于树巢……”——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第六十五页《昆仑》。
山名叫做昆仑,国名也叫做昆仑,洋名也叫昆仑,昆仑是南洋诸国王的姓,大臣的官号,看:
“隋时其国王姓古龙,诸国皆姓古龙,讯耆老言:古龙无姓氏,乃昆仑之讹。”——《通典》卷一八八,《扶南国》。
“其大臣曰教郎索滥,次曰昆仑帝也。又次曰昆仑教和,次曰昆仑帝索甘。其言昆仑古龙声相近,故或谓为古龙者。”——同上,《槃槃国》。
由于有昆仑洋、昆仑山、昆仑国,就推而远之,把属于这一带人的叫做昆仑人。
二
昆仑是黑人即马来人种的一个专名词,专指一种拳发黑身的人种。所以这名词在中国后来就变成一种黑色的人的形容词,如:
“李太后初为宫人,在织坊中,长而黑,宫人谓之昆仑。”——《晋书》
“慕容彦超称阎昆仑”——《五代史》
“真定墨君和,眉目棱岸,肌肤若铁,年十五六,赵王镕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即呼为墨昆仑,即以皂衣赐之……当时间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刘氏耳日记》
“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先是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凉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与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幽间鼓吹》(按康昆仑并见《国史补》“韦应物”条及《太平广记》卷二。五“汉中王瑀”条。)
文人学士有时也拿昆仑来做对象描写或开一点无害于事的玩笑。如:
“‘狂生崔涯与张祜齐名’。嘲一妓云:‘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五。
“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宫,……”——唐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七一五至八一五)
“苏颋初未为父瓌所知,后见颋咏昆仑奴诗:‘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为客所称,乃稍亲之。”——《开元传信记》
把以上的例记归结起来说,我们知道在八世纪时已经有人拿昆仑奴来做题材写诗,有人把昆仑做混名,有人拿昆仑儿来开玩笑。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在七世纪时昆仑奴已经普遍地为中国人所知,或者也已经普遍地为中国的有产阶级所豢养了。
所在再进一步地来说明昆仑奴的来路。
A.“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蹈曲为乐。”——《文献通考·四裔考·三佛齐》
B.“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遣使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同上,《大食》。
C.“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一一七八)。
D.“昆仑层期国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蚪发,诱以食而擒之,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至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宋赵汝适《诸蕃志·海上亲国》(一二四二至一二五八)。
E.“沙华公国,其人多出大海劫夺,得人缚而卖之闭婆。”——同上。
F.“波斯国在西南海上,其人肌里甚黑,鬓发皆蚪……无城廓。”——同上。(按此为马来波斯非伊兰波斯)
G.“番官勇猛,与东边贼国——丹重、布哕、琶离、孙他——故论——为姻。彼以省亲为名,番舶时遭劫掠之患,甚至俘人,以为奇货,每人换金三两或二两。……土人壮健凶恶,色黑而红,裸体文身,翦发跣足。”——同上,《苏吉丹》。
H.“买人为奴婢,每一男子,鬻金三两,准香货酬之。”——同上,《占城》。
I.“外国贼舟……多就是港口抢劫本地人往别国卖,每一人鬻金四两或五两。”——《事林广记》卷八《岛夷杂志·佛哕安》
J.“海岛内有野人,身如漆,国人布食诱捉,卖与蕃商作奴。”——同上,《昆仑层期国》。
K.“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独可卖,往货取以鬻,折杖以识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南海异事》
L.“洪武三年(一三七○)王昔里八达刺遣使奉金等表贡方物及黑奴三百人。”——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三《下港》(按《星明四夷考》卷上爪哇所载与此同)(一六一七)
M.“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世,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之以供祭,每人得值三金。”——同上卷四,《彭亨》。
据AB三佛齐大食有昆仑奴,据D大食的昆仑奴是由昆仑层期国掠卖来的。昆仑奴的出产地据CDEFGHIJK是昆仑层期国、沙华公国、波斯国、苏吉丹、占城、佛哕安、南海,许多属于南洋群岛尤其是附近安南爪哇的几个小岛,是属于马来人种的血统的野人。获得的方法是由于掠夺,惟有K是由父母出卖的。昆仑奴的价格,通常是由二金至五金,不如命(意?)的可以杀死祭神,去路是大食、阁婆、(爪哇)、三佛齐(旧港)以及各地的蕃商。到中国来的手续,如L是由爪哇国王贡献三百人,因为接壤的关系,或由安南暹罗三佛齐爪哇诸地间接输入。或由商业关系,从蕃商或本国的商人输入。据《隋书》及《通典》所载,则由于宗主国的关系,来服兵役或来当奴隶,均属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假设。
三
两广一带因为与南洋接壤的关系,所以蓄养昆仑奴的特别多。
“宋世广中富人多蓄黑奴,有一种人水眼不眩者谓之昆仑奴。”——朱或《可谈》
喜欢蓄养黑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亲属之恋,可托管钥,更特别因为他们耐劳而且有特别的技能,他们来自水国,当然他们更习惯于水,由于这个概念,就形成了下列的几个故事。
“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右而往省焉,……赠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甘泽谣·陶岘传》出《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
“唐周郁自蜀沿流尝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原化记》出《太平广记》卷二二三。
“故大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入,遂召船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唐刘恂《岭表录异》
更因为昆仑奴的容貌凶猛丑恶,习惯言语宗教不与中国人同的缘故,由于好奇心的刺发,形成了下面的一个故事,使昆仑奴成为一个与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
“唐大历中(七六七至七七九)有崔生者,为千牛。往视勋臣一品疾。一品命一衣红绡妓擎一瓯与生食,生郝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进之。生去,一品命红绡妓送出,生既归,神迷意夺。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负生入一品宅,达红绡所,复负生与红绡出,红绡遂归于生。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裴金刑传奇》,出《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把一个浑浑噩噩的昆仑奴,侠化神化成为一个勇敢、聪明,武艺绝人,义侠,飘忽的典型人物,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十世纪人的尚武文学的观念与时代背景及昆仑奴的奴隶制度的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
“到天坛南,遇一昆仑奴,驾一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奴扶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续玄怪录·张老传》
这一段故事的意义表明了在唐宋时代的奴隶制度中的昆仑奴的蓄养的普遍化,虽然是一个神话,一个由闭着眼说鬼话的道士或无聊文人所造作的神话,不过无论如何多少总含有一点时代的真实性的。这一点由时代所给予的真实性的。这一点由时代所给予的背景,就为我们解释了当时的昆仑奴的生活状况。
在唐末的时候,似乎广州的昆仑奴的数额已经突变的激进,据外人某种文献说,黄巢破广州的时候,屠杀了外国人十二万,这话也许可信,大约这时期广州的昆仑奴因数额的增进,他们潜在的势力也跟着增进了,一旦高压力过重,就生出一种伟大的自然的反抗出来:
“广州刺史路元璇,渎货无厌,多所渔虐;一昆仑奴入后堂割其首去,群昆仑奴和之,遂陷广州。”(忘出何书)。
这是惟一的昆仑奴的自动的革命,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材料中,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件事,足以代表昆仑奴的反抗的事实的。
汉代之巫风
一 巫
汉代巫风特盛,武帝世巫蛊之祸,是两汉史中的一件大事。
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浑浑噩噩,以为风吹草动,星辰运行,甚至一石一木都有不可知的神秘在凭借着。由惊奇而恐惧,由恐惧而彷徨,由彷徨无所主而发生一种时常在动摇不定的物的崇拜,渐进而成为信仰,成为原始的宗教。替他们解释这神秘,领导着举行宗教的仪式的便是所谓巫和觋。但任这职司的人,大抵都属于族中的耆老,因为他们经验多,识见广,逐渐地成为世袭的耑业,作一氏族中的指导者。
《国语·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中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巫的职司是乐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之。”商书:“敢有恒舞於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疏谓:“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巫又能前知;荀子:“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又长祝咀;《史记·封禅书》:“太初元年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咀匈奴大宛焉。”擅祓除求雨之术;周礼春官:“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沐,旱嗅则舞雩。”
汉兴,尤重巫祝。《汉书·郊祀志上》:“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祀宫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縻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时日。”女巫以国家功令所祠的对象不伦不类地什么,天,地,山,水,神,鬼,怪物,老巫,……一起都被按期举行着古怪的典礼,保存着古代的习尚。
除上述地点以外,齐陈二地因历史的背景,巫风亦极盛。《汉书·地理志》记齐有巫儿:“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日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这颇和近代一本反对基督教的书——《辟邪纪略》中所记“玛丽”的教徒习惯相仿。)又云:“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巫是女人,所以能出入宫禁,作压禳诅咒的勾当。(《汉书》公孙贺传,江充传,戾太子传。)
二 神君与西王母
女巫所祠的神中最著是《封禅书》的神君。这故事荒唐得很有意思。对于西王母故事有兴趣的学者,常疑心为什么后来的著述家喜欢把汉武帝作西王母故事中的一个主角?这因缘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这一有趣的问题,我们企图在本文中作一比较的解答。《封禅书》中的神君故事如下:
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见注)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土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文成死明年,天于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日: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属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帷室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在后出的《洞冥记》中,我们发现一段故事,和神君极有关系:
元光中,帝起灵寿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斗。洒其叶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亦日珍珠树。此坛高八尺。帝使董谒乘云霞之辇以升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元鸾,歌春归乐。谒乃闻王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止。坛旁草树枝叶,或翻或动,歌之感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