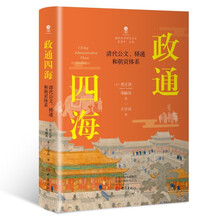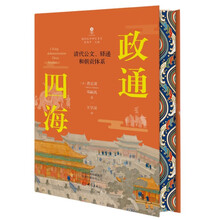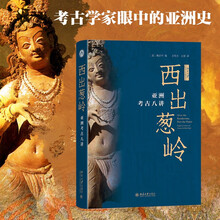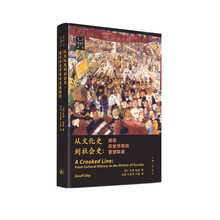明烛无端为谁烧?——清代朝鲜朝贡使眼中的蓟州安、杨庙 葛兆光
各种过去的遗迹诸如祠堂、庙宇、牌坊、碑铭,等等,常常作为象征,为历史储存着种种记忆。历史记忆有深也有浅,有的能激活,有的却隐没不见。通常,这些储存记忆的象征并不开口说话,所以,要靠后人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呈现出“意义”,所谓“传统”,所谓“文化”,也就在这种变动的记忆和想象中延续。可是,据说历史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有根有据的想象”,想象却因人而异,同一历史象征在不同阶层的人群或不同文化的族群中,会引出不同记忆和解读,记忆和想象中重现的那个“历史”,也因为立场、处境、心情的不同而呈现了不同的“意义”。所以有人干脆说,历史记忆其实只是对当下的想象和对传统的解释。
正如莫利斯·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说,记忆虽然往往只是个人的记录,但呈现的是这个人所从属的群体意识,不同群体(groups)中的人们,对同一事情的记忆往往不同,更何况不同族群。特别是当曾经共享一个传统的两个族群,开始彼此心生嫌隙,却又互相谛观时,各自又会在对方的历史遗迹中,衍生出种种有关异邦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型塑对手,也在这种想象中建构自我。清代二百多年里,朝鲜朝贡或谢恩的使团每年都要经过蓟州城外的翠屏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看到这里有两座奇怪的庙宇和罕见的祭祀,这个时候,他们想到的历史,他们解释的现实,就很有这个意味。
一 蓟州城外翠屏山
我没有去过蓟州城外的翠屏山,甚至也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过它,可是,我在朝鲜朝贡使和贺岁使的文献里面,却屡屡看到这座山。那时,来北京的朝鲜人很多,他们在日记里面反复提到它。之所以朝鲜人总是记述它,是因为当时山上山下有两个庙,而庙里供奉的人物让他们对一直仰望和崇敬的中华上国文明产生了一些惊讶,而这惊讶又渐渐变成了鄙夷。而这种对大清帝国文明的鄙夷,在他们心里,又很奇怪地转换成对本国文明的自豪和自信。
公元1699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的冬天,朝鲜人姜铣奉命随冬至谢恩使团出使北京,好容易到了北京附近的蓟州,在州城西门外的翠屏山下五里桥,他无意中看到,“桥之旁设庙堂,置女人土塑于桌上,俗云杨贵妃画像。又设一庙堂于山上,谓之安禄山画像”,行程匆匆,让他来不及去仔细查看,他只是在日记里面记了一笔,。三百年后,我们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只是猜想,他特别记上一笔,是因为他觉得太奇怪了,通常只应该祭祀神灵、英雄和忠臣的庙,怎么可以供奉这等人物?更奇怪的是,怎么可以既供奉唐代天宝末被缢死于马嵬坡的杨贵妃,又供着造成唐帝国由盛而衰,也连累杨氏之死的逆贼安禄山?虽然说,以前大明帝国也曾经是淫祀遍地,正如明代朝鲜朝贡使者所看到的,“中朝最尚异教淫祠,每村必有一寺,或有三四者,谓之庙堂,每朔望焚香礼拜,城中亦有庙堂数处……”但是,好像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北京城外,居然有这么奇怪的祠祀!
不知是军事机密的考虑还是供给方便的原因,大清帝国对于朝鲜朝贡使行走的路线有严格的规定,使团从义州渡鸭绿江人栅门经凤凰城之后,过辽东抵沈阳,经山海关至丰润,到北京之前一定要经过蓟州城,所以,年年朝鲜使者都看同样的风景,也常常会发同样的感慨。六年以后,另一个朝鲜使者李颐命(1658-1722)再
次路过这里,看到这个奇怪的景象,联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想,自居易居然还写唐明皇让鸿都道士“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寻找杨贵妃,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白居易会觉得李、杨之爱“此恨绵绵无绝期”,左思右想,就愤愤地写了一首诗,讽刺这个奇怪的祭祀,连同讽刺这个名贯遐迩的诗人和他的名篇《长恨歌》:
渔阳遗俗尚淫祠,妃子终归锦襁儿。地下明皇能悟未,鸿都道士果逢谁。
想到旧时传说中关于杨贵妃和安禄山的传闻,另一个差不多同时的使者崔启翁(1654_?)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虽然含蓄委婉,但讽刺之意也很清楚:
杨妃初不产渔阳,遗像如何在道旁。知是禄山真配匹,故有双庙两相望。
他们讽刺唐玄宗说,这个昏君到老,居然还那么怀念马嵬坡下缢死的女人,其实,她的心也许早已不属于皇帝,而属于那个胡儿叛臣,而他们对这两座庙的讽刺,意思则是百姓无知,居然也相信这种荒唐想象故事,胡乱搭配,祭祀妖神野鬼。
二 入祠无客不伤心?
“马嵬坡下草青青,至今犹有妃子陵。题壁有诗皆抱恨,入祠无客不伤心。万里西巡君请去,何劳雨夜叹闻铃。”这是天津小彩舞骆玉笙的名段《剑阁闻铃》,当你听到那苍凉的声音唱到“不作美的雨呀,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的时候,总觉得有些意思在,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远离盛唐的难忘记忆,仅仅就李隆基、杨玉环个人情感而言,白居易一首《长恨歌》,洪舁一出《长生殿》,让他们似乎真的是“恩爱夫妻世世同”了。只是,其中有一句“悔不该兵权错付卿义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从兄”,仍然透露了后世编戏人对大唐几乎倾覆的历史回忆中,还是有追究杨贵妃误国的意思在,历史评价在文学想象中也始终存在。
不过,好奇和想象却常常借助回忆和文学在历史中驰骋,并不是今天才有“戏说历史”的习惯,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虽然历史学家总是希望努力探访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分正邪、别善恶,让后人见贤思齐,逢恶自戒,偏偏普通民众对于历史有另类想象和解读,好在宫墙外窥伺宫闱内的秘事,大概是很常见的事情。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说,安禄山在皇上面前应对的时候,常常“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座”,这个糊涂的唐玄宗却让杨家三姐妹和安禄山结为兄弟,面对美人,使得安禄山很动心,“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此后的传闻越来越多,《旧唐书·安禄山传》加上了安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入对先拜太真,后拜玄宗,还让安禄山自己解释说,这是蕃人“先母而后父”的习惯,再后来,添上了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异闻,甚至在《天宝遗事诸宫调》中,还加上了杨妃洗澡和安禄山戏杨贵妃的色情段子,明明白白地呈现了民众窥伺宫闱秘事的好奇,也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常人对于政治的判断,原来一对淫男乱女,女是红颜祸水,男是夷狄后裔,一道来祸害李家天下,生生地把这好端端的盛唐变成了战端四起的乱世。
没有什么比绯闻更加吸引一般人的眼睛,也没有什么比义愤更能表达普通人的道德,想象加上想象,传闻添上异闻,就像滚雪球。于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两个人,好也罢歹也罢,便纠缠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正好像如今的“戏说”,本来并无须对谁负责,只是在这种近乎无厘头的“戏说”中,透露出一般思想世界的观念和愿望,而这种观念和愿望被塑形成像,供进庙里,又无时无刻地不在传达着民众的艳羡、窥伺和揣测。写在颜面上的民众观念和世俗愿望,被自居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一眼望见,他们的脸上便有些不屑的表情。
朝鲜人有理由不屑。他们在从栅门到北京的千里路上,看到了华夏文明似乎在颓败,康熙三年(1664)奉命出使北京的洪命夏,看到闾阳的明伦堂堆满了柴草,就感叹“庙庑颓落,惨不忍见”,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的韩德厚,更看到山海关堂皇佛寺附近衰颓的文昌宫,也感叹“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他们说,现在的中国崇拜,以佛陀、关帝、孔子为序,这是彻底坏了儒家规矩。说的并没有错,就说清代的蓟州城内外罢,除了当时北方处处皆有的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八蜡庙、文昌庙、武庙、火神庙、马神庙、灶君庙、玉皇庙之外,还有东岳庙六座、药王庙十一座、真武庙十二座,而关帝庙竟然多达二十二座,所以,在笃信儒家学说的朝鲜人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只好说,“文物沦陷已久,亦已悲矣,其俗最好尊佛事鬼,虽数户之村,必置庙设像,孤孀之家,亦架壁礼神,人鬼互居,僧俗杂处”。所以,对于这一类没有来由的淫祠淫祀,一壁厢他们有格外的愤怒,一壁厢也是满心鄙夷。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同金昌业出使北京的赵荣福看到山下“浑体涂金如佛躯之戴冕执圭”的杨贵妃塑像,和山上宏丽庙宇中端坐的安禄山,甚至和安禄山一道居然还有唐玄宗,就觉得骇讶得难以接受¨。九年后(1721),一个叫作李正臣的使者再次经过这里。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路旁小庵,设杨贵妃塑像,军官辈历入见之,口言,初闻障画,见之则塑像,非涂彩也,乃涂金云。自此杨妃院相距五里许,北边山麓上有安禄山院堂云,问此山名,乃乌鸣山云。此等淫祠,甚无意义,此必盲俗因禄山之曾守此地而然,而至于杨妃,尤出于附会,可骇可笑。
三 或是夷狄旧时风?
本来,这种胡乱祭祀的事情无处不有,古代中国的官方和士大夫,曾经很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对这种虚幻世界加以控制,历代对淫祠淫祀的禁令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政治意愿,不过古代官方的管束力量却有限,所以常常是提倡有余,禁毁不足。因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是官方觉得可资鉴戒,有表彰必要的呢,便赐额封号,让它合法化;若是它只是地方迷信而无教化意味呢,则听之任之,在历史记录中故意遗忘。这是古代中国的常规,打宋代以来就是这样,不止是大清王朝。不过,在始终认定只有大明才算华夏文化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那里,这种淫祠淫祀的荒唐,便一股脑儿归咎到了他们视为“蛮夷”的清帝国身上。
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和李宜显一道去北京途中,看到这个怪现象,就说,安禄山是唐王朝之叛贼,有什么功劳受到祭祀?他们猜想,也许是因为安禄山曾经当过这里的节度使,所以其后的节度使如史思明、田承嗣辈,就尊奉安禄山,立祠于此地吧。可是,他们又质疑说,宋代和明代都是汉族人的政权,对这种胡风淫祠何以会不管呢?“宋明继唐而有天下,且成祖开都于北京,蓟即畿服也。叛乱如禄山,而仍置其祠,终不毁去者,又何耶?”说到这里,他们仍然不甘心,便接着下一断语说,清人是夷狄,蛮夷修这种庙宇,当然不足为怪。
这些朝鲜士人对清王朝多少有一些种族的偏见,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起清王朝来,中华文化的血脉更加纯正,著名的洪大容在记载汉族士人葛官人和朝鲜人金复瑞的对话时,就显示出这种表面谦恭下的极度自负,“(葛官人)问东国风俗。(金)复瑞略对以尊朱子、妇人不改嫁等数事。(葛)官人皆称善。又问:今见中国,比东国何如?复瑞云:外国偏小俗薄,文胜何敢望中国。官人日:朝鲜乃箕子之地,宁自同于外国乎?复瑞日:中国虽大,蒙古、回部杂处,辇毂衣冠淆乱,无复分别,此可惜也。官人熟视良久,大书‘呜呼’二字,却坐仰天而笑”。汉族士人的自我颓废和自惭形秽,让他们觉得自已在政治正确之外还有文化上的优越。特别是大清王朝为了证明自己,而对于传统的着意修饰,也真的露出了很多让朝鲜人一把揪住的把柄,像李德懋在沈阳书院看孔子塑像时,就联想到明朝在孔庙里用牌位代替孔子,觉得还真是英明,因为“金时孔子塑像,皆剃鬟左衽,天下之大变也”。尽管这里的孔子,倒是“儒衣儒冠,俨然而坐”,但是“眼稍圆,唇褰而齿现,面黄赤,旁有子路立像,恐涉猥亵”,他觉得,清朝皇帝是女真后裔,所以才会在康熙时代出现道州周元公后裔把周濂溪塑成怪模样的事情,这和金代“孔子像剃鬟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