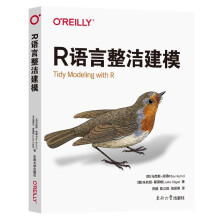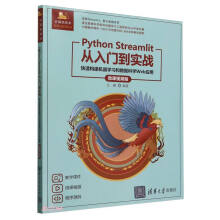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流行戏剧更能表现民众的品性。<br> 每个时代的喜剧都是为那个时代的民众竖起的镜子,一面独特的镜子。<br> 当大幕升起,古罗马的精彩大戏就要在我们眼前上演时,让人吃惊的是,拉起大幕的是两个喜剧作家。在这个庄严舞台上,他们是最先现身的人。流传至今的罗马文学中,最早的作品是喜剧集。再早我们只知道两个作家,他们的作品早已湮没无存,唯余残篇。不仅拉丁文学,还有我们关于罗马的直接认识,都来自喜剧,并且不是那种粗俗的民间喜剧,而是丰赡曲致,真正的喜剧格调。这个事实,很少有人琢磨,其实让人费解。教育和书本给我们植入了关于罗马人的观念:从不屈服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更严格、更坚定、更严肃。让人忐忑的是,我们这种认识的源头却和这些观念正好相反。按照我们的观念,世界之王的文学作品应该以有关战争的、激动人心的事情作为发端,是有关勇士和战绩的古老歌谣,由慷慨激昂的行吟诗人吟唱,在一部伟大的史诗即拉丁文的“伊利亚特”(指《埃涅阿斯纪》——译注)中达到巅峰。但文学的世界有多广阔,罗马文学实际的起点就离我们的这个观念有多远,它的起点就是一系列喜剧,人们普遍认为它们是建立在当时民间的希腊喜剧基础之上。<br> 再没有其他哪个伟大国家,其文学之源竟是完完全全的外来物。在希腊,文学的发展是自然的,产生于通过El口相传和无数未知时代的修补而传承下来的歌曲故事。在人们——农夫、牧人、战士——心中有自然的愿望,想要形象地表达,它们最终形成文学形式,千古存留。罗马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文学形式最早是,漂洋过海,从希腊而来。发现有现成的形式正好合适,表达的愿望才随之而来,所以愿望只在其次。若想论及罗马精神,这个事实意味深长。 <br> 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的一代人中突然出现;而且不仅喜剧,其他所有一切都以希腊为典范。在别处,几乎很难看到本国文化被国外舶来品取而代之。我们确实发现一种罗马特有的韵律,它与第一位翻译希腊文学的人运用的韵律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还发现,后来的作家引用了他们在童年时代听到的若干歌谣;不过,这就是古罗马本土文学的全部。或许罗马农民和牧人以强烈的务实态度闻名后世,很不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吟歌弄曲、编排故事,或许后来终于登场的文人们关注那些向化外找寻文化并且很快满载而归的作家,而轻视民间文化,无论真相如何,事实让人震惊。罗马民族对诗歌的感觉并不强烈。他们自然的天资不是催迫他们去做艺术的表达。传说,罗马建于公元前753年,而我们知道的最早的罗马文学作品,《奥德赛》的译本,出现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罗马建城约五百年后。在这数百年间,不管世界向罗马人展示了什么,或者生命带给了他们什么,似乎他们都很少有冲动以任何形式去传达。后来,罗马批评家提到一种本土的喜剧,是节庆时即兴的表演,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它曾形于文字,可以肯定的倒是,它没有直接的文学传续。<br> 对我们来说,罗马文学始于普劳图斯,一个模仿希腊风格的喜剧作家,他向我们展示的罗马生活是我们对罗马的第一瞥。这是简单的一瞥。为他和泰伦斯——他的后继者——掀起的大幕,很快便又落下。当大幕再次掀起,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西塞罗的时代。除去一篇讨论农业的文章——诡异的是,这是加图,一位笃定而老迈的道德判官的作品——存留,在这期问我们有的只是一些文学的碎片,没有确凿的材料来重新搭建这个城邦,而这时它已经称霸于世界。是的,当两个喜剧家中更为年轻的泰伦斯创作戏剧时,希腊人波力庇阿斯正在创作一部记述罗马强权兴起、强盛的伟大史撰,其中很大部分保存了下来。但他关注的是罗马的战争,以及作为战士的罗马民众。直到公元前1世纪,关于罗马生活的其他部分,同时代人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都只是来自这两位戏剧家的作品。<br> 我们或许是幸运的,因为留存下来的是喜剧。无论什么时代,没有什么比民众看的戏更能反映他们的模样。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比流行戏剧更能表现民众的品性。而喜剧作用尤甚。喜剧必须——悲剧就不必——向观众展示他们熟知的真切的生活画面。每个时代的喜剧都是为那个时代民众立起的镜子,一面独特的镜子。古代喜剧传到我们这里,仅存四位剧作家的作品,他们是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以及罗马的普劳图斯和泰伦斯;这些作品是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希腊和罗马人得到了生动再现,而且他们正处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时期:希腊最光辉的岁月——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艺术中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以及紧随其后的时光;以及百年之后的罗马,这时迦太基已经两次被击败,罗马文明的基石已经牢牢奠立,我们自己的文明直接溯源于斯。关于古代这两个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把它们建立起来的人民,作为凡夫俗子的男男女女,是何种模样,而这些,那部关注他们的战争和法律的历史著作却很少向我们描述。他们是剧场——主要是喜剧剧场——里的芸芸众生。只有在剧场我们才能发现他们。流行喜剧说的就是平常人。<br> 如果希腊悲剧散佚,我们有的只是阿里斯托芬,那么关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平民仍然会有非常周全的观念。阿里斯托芬的每部戏剧都表现出他和其他地方的戏剧家多么不可同日而语,他想要的娱乐多么与众不同。阿里斯托芬有他自己的喜剧概念,可谓前无古人,当然也后无来者,他自己也这么告诉我们。《马蜂》与《和平》的合唱部分,展现了这位雅典最著名的戏剧家招引观众的手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