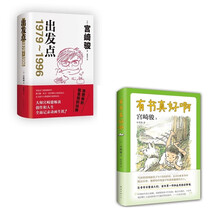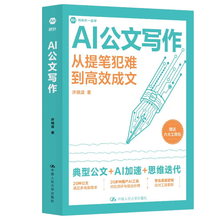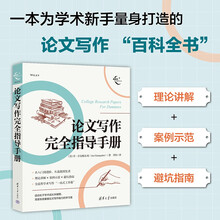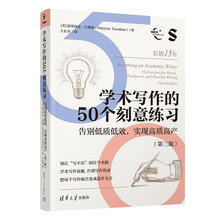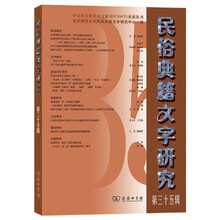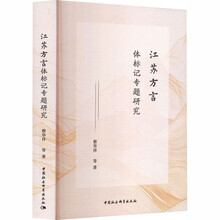第一章 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
【提要】本章讨论中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以历史观点看,中国翻译成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学科,与领域内其他体系互动,可以更有效地发展其理论个性。因此,不能将各种语言文化间的不同之处看作是互动的障碍,或者是对所声称的中国翻译独一无二的特色的支持。超国界的中文研究过去是、将来也永远会是全球翻译研究大系的一部分。据此,我们要下功夫强化中国翻译的哲学基础,扩大其研究视野,改善其研究方法,以利于国际间的互动。
1.0 引言
1996年初,于国际译联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之后在澳大利亚的迪京大学举行的口笔译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是:中国国内有人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问题,含蓄地表达了国际译学界对中国大陆近年来产生的一种守成型的研究心态和研究取向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说是衍生于对加强交流的期盼(如R.阿埃瑟朗,见许钧1996:2,8),也是触发笔者思考中国翻译研究中的所谓“自成体系”和“特色”论的一个契机。本章旨在说明,这两个说法,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而对它们的过分强调,已经成了中国译学中的两个误区,既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也影响了中国译学体系与世界其他译学体系的互动。
1.1 中国翻译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1.1.1 “成体系”与“自成体系”之别
在罗新璋(1983/84)的文章发表之后,“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这一说法可谓在中国译学界不胫而走,尽管并非得到所有论者无保留的一致认同。罗文的确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但如果放在历史的高度来看的话,其贡献更多的应该是在于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实践和名家观点进行了有系统的梳理、总结和综述。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名家观点,有的只是一种“意见”,借用谭载喜(1998:13)的说法,是“偏论”、“散论”而非“主论”、“专论”,也就是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这一点,作者本人也承认的(罗新璋1983/84:601)。
但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系统中,作者看到并揭示了这些偏论、散论之间的联系及其继承关系,因此认定它们是成“系统”(可否理解为system?)的,由“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贯穿成发展主线(另参见赵秀明1996:37)。对历史的梳理总结,可以说是罗文的一大贡献。然而,说这些散论偏论可以结合而“自成体系(system?institution?)”,那就在逻辑和认识上值得商榷了。首先,“自”字所本的,如果是同时以国界、国籍、血统、语言等四个界定因素定义的狭义“中国翻译”(关于“中国翻译”的逻辑定义,参见第二章有关论述。在本章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中国翻译/译学”以狭义解,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翻译及其研究;而“中文翻译/译学”一语指的就是单以语言文化界定的广义的“中国翻译”,其中“中文”包含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文字等构成民族性的成分),那单以国境线为界,任何一个国家内对翻译(或其他人们感兴趣的课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集腋成裘”地说是“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之“自成体系”一说,也就失去意义了。其次,如果我们采用单纯以语言文化定义的广义的“中国翻译”,那罗文中并没有对其他语言文化体系间的翻译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同“中国翻译”对比而彰显出后者的“自”有或“独具”特色来。因此,在缺乏进一步证据与论证的情况下,“自成体系”的认定便只能是个假定了。在这一点上,董秋斯是保持了一个较为冷静客观的立场的: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仅[尽]管这些东西是很可宝贵的,有过很大的功效,但是,无可讳言,不能合成一个体系。一种体系的构成,是一种广泛地调查研究的总结。(董秋斯1950/84:25)
至少,罗文提出“自成体系”一说,但并未驳倒董秋斯对体系概念的上述基本界定。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提出的说法,如“神似”与“化境”,本身既不是成体系的论述,也不见得就是外国没有的“特色”。如当年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借用柯勒律治(Coleridge)描述人性和圣灵的结合来说明翻译时,
其比喻就与“化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与原作合二为一,惟此方可成佳译。二者结合,端赖相互间之迷雾——于译者言乃思想、言说、情感诸方式相异所生之迷雾——能否“排解至纯然透明”而不复见。(MatthewArnold,见Robbinsonl997:253)
其“同工”之处,用张柏然和姜秋霞(1997:7)的话说,就是“[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锺书的‘化境’说]都局限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概念上应该进一步澄清的是,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一个系统,但并不等于可以自动形成一套成体系的理论。如果声称是成体系的,那就得严密地论证出该体系的(共同)哲学基础、理论架构和术语系统等基本要素的存在。而这正是中国译学目前尚待开发的一个领域。
1.1.2 “回顾”与“规定”之别
尽管如此,罗文作为对历史的总结,按其标题和总的内容所示,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回顾性的表述评说,本身并没有包含、暗示或规定现代人应该对这一体系要采取什么态度。整篇论文本意,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应该也是“绝无牢笼以后之意”(罗新璋1983/84:601)。问题在于,中国人尊崇传统的这一心理模式往往又会营造出一种把传统神圣化、绝对化的氛围(许苏民,见孙荪1992:540—42)。(应该附带指出的是,把传统神圣化、绝对化同发扬继承传统是两回事,而在翻译学术之外的领域如道德和文化,一个民族更是完全有权有义务维护自己的传统的。)而罗文在最后一句(页604),也颇有点动感情地通过呼吁而“规定”(prescribe):“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如果“自成体系”的认定只能是个假定的话,那“卓然独立”便失去了依托,而这种独立与特色能为中文翻译提供多大的理论优势,更就成为见仁见智的猜测或多少带有感情偏爱的武断了。
这一回顾性表述后来的话语演变可以为上述论点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当人们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这一封闭的定中结构短语演化成“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这一开放的主谓结构句子时,一个回顾性的现象表述就变成一个判断了(在缺乏论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被简单化为一句口号,事实也往往如此)。因为作为一个陈述句,它的开放系统为表示个人解释的情态动词留下了空间,比如说,在接受者的潜意识里,可以读作:“中国翻译(过去曾经是、将来必定还是/一定是/必须是/可以是/应该是/永远是/……)自成体系。”各种解读在接受者潜意识里相互作用,潜移默化中鼓励了一种封闭心态,或者一种不容比较的极端对立。如果推到极致,这就成了“自说自话”的所谓理论,一种劳陇(1996:41)所称的“空洞”的理论得以产生的认识论基础。
在现实中,“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常常也是作为前瞻性的判断被引用的,如“(……)建立起自成一体的学派,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事”(许钧1997:5)。应该说明的是,当我们说一个理论“成体系”时,这个体系是开放的,起码没把它关上。可是当我们把它说成是“自成体系”的时候,这个体系便呈现为排他性的,倾向于关闭了;而在演绎中更有可能(实际上也经常是这样)把“自成”推导成是可以或应该“自外”于其他体系而存在的体系了。
一个理论,强调其个性和独创性,证明其结构有个可依托的基本体系,是该理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自省过程中的着眼点。一个个别的翻译理论体系,不管是正在形成还是已经形成,只能是同整个翻译研究知识体系,进而同人类的大知识体系相联系的一个“次体系”。这个次体系,因其创新的视点、开拓性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而获得体系间公认的理论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纯粹学术意义上的“学派”,不是主观地、先入地去努力“建立”或自我标榜而成的,而是客观地事后“形成”的。)同时,这样一个开放的(次)体系有能力通过与其他次体系的互动而持续发展,并为整个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为整个人类的大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和精密化做出贡献。
1.1.3 比较:“盲融的优越感”与“有根据的自尊心”之别
事实上,许多论者都指出(尽管很多是停留于印象化的表述)中国译论和其他译论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如许钧(1996:4)。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有一点似乎是非常相似的,如许钧(1998:5)报告说,“乔治?穆南(……)认为在本世纪之前,涉及翻译的文字大多为经验之谈,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少有科学的探索”。可以认为,在语言学发展之前对翻译的研究,整个是处于其“幼年期”,大部分的讨论“凭的是趣味和秉性而非知识”(Bates1943:15)。用谭载喜(1998:13)的话说,就是“[世界性的翻译理论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偏论、散论到主论、专论的发展过程”。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翻译理论,整个还处在探索发展之中(注意,探索与发展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翻译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还期待人们去探索”(R.阿埃瑟朗,见许钧1996:3)。
因此,环顾世界,我们似乎无需为中国早期译学中各自不成体系的经验之谈或目前在有些方面的不够成熟而耿耿于怀或自惭形秽,更不用从一种盲目的自卑感演变成盲目的优越感,大而统之地声称“就整个译论发展或全部资料来看,[中国这些貌似不成系统的译论]却是彼此贯通,共成体系的”(如上所述,给出这样宽泛的条件,那全世界的译论都可以既“自成体系”又“共成体系”的);或者以“西方译论所讨论过的内容,我们的前辈一样探索过”来证明中国译论“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有的甚至“是西方译论望尘莫及的”[本段引文均出自赵秀明1996:37;关于以“古已有之”来证明华夏文化的至高无上这一心理模式,见黎红雷(孙荪l992:542—43)]。
无论是否赞成“自成体系”说,我们都会拿中国的译学同其他译学体系比较的(关于比较,除本节外,另见下一节讨论)。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比较中需要避免因为不自觉地以(民族)情感为出发点加上价值判断的介入而落入认识上的谬误。比如有人警告说,“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董史良1997:5)。这个论断在逻辑上就经不起推敲。一个有其合理性的理论,不管是谁的(前人的、今人的、中国人的、外国人的),都无法把它批(只要是理性的批判而非感性的评判或出于其他目的的“宣判”)得“体无完肤”,而一个可以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理论,不管是谁的,不摒弃要留着又能如何推动(我们的或别人的)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发展?
因此相反的,在比较中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客观理性的立场。比如同样基于“古已有之”,方梦之(1996:5)就得出了一个客观的、发展的观点:“现代译学的一些核心思想我国译家早有表述,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这就需要融合吸收外来新理论使之发展”。这种建设性的态度隐含了一个对中国译学现状的挑战,这就是,应该如何融合吸收外来理论以保证自身可持续地发展呢?从目前看,在融合吸收外来理论的过程中,根本的还应该是了解特定理论背后的形而上的研究哲学、思想方法,形而下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能以新的视点、新的方法,从新的哲学深度来观照与汉语有关的翻译现象,最终从汉语这一角度提出现代化的、国际化的理论(theories),与非汉语的译论进行对话(criticalengagement),为整个世界的翻译研究提出新见解、开拓新视野,再进一步通过对翻译的研究,使整个人类对世界及人性的观察和认识更为精密。正是以这种客观的总结和理性的前瞻为根据,我们可以建立起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1.2 中国译学的理论个性是在国际互动中发展的
1.2.1 “中国特色”:出发点还是目的地?
由于一个本来是回顾性的表述于不知不觉中演变成规定性的呼吁,于是在中国译学展望未来之际,出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提法,那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不但已经成为一个口号,而且要成为一项任务。在这个阶段,中国译学,往后看是“自成体系”,往前看又要保持或发展自己所声称的独具的特色,一脉相承。但是,单单以“自成体系”作为提出这口号的理据是不充分的。
比如说,要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作为任务因此也就是目的提出来,那无意中隐含的前提便是以下三个之一:中国译学目前既没有中国特色也没有理论;中国译学目前有中国特色但没有理论;或者中国译学目前有理论但没有中国特色。无论是哪一个前提,都与中国译学现状不符,都会给中国译学带来认同危机。其实,以中国语言文化现实为一个立足点的中文翻译研究,“中文特色”是其天然的研究出发点(而非终极目标)。以其独特的出发点溶入体系间互动研究的主流,从而在整体(通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也是它在发展过程中能为国际译学做贡献的特质之一。如果因为狭义地理解“中国翻译”而把出发点与目的地等同起来,那就谈不上实质性发展或自我超越而成“通用理论”(generaltheory)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