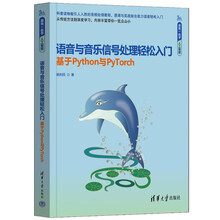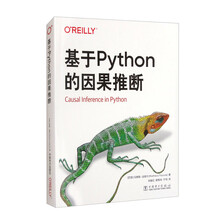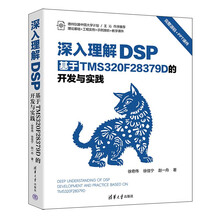我于1949年9月24日出生,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喜悦,却也增添了负担和烦恼。父母在小镇上做小本生意勉强维持全家生计。母亲吴招英13岁嫁到高家,17岁生育第1个孩子,轮到我出生时,母亲已30岁,我排第9,前面8个孩子都因病夭折了,我成了老大。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姐姐经常抱着我,她叫菜仔,大我四五岁,她八九岁时,又因患脑膜炎走了。可怜的母亲为子女哭干了眼泪,母亲将我视为珍宝。小时候,母亲为我算过多次“八字”,拜过许多菩萨,还在我的左耳戴上金耳环,生怕丢失。记得一次测字先生拿着我抽的签说:“懵懵懂懂,挑担水桶,掉了一桶,不知轻重。”说我走的是懵懂运。为了我,父母不知吵过多少次架,家庭原来的平静因我而打破。我3岁以后,母亲又先后生下两男一女,全家6口人。全靠父亲高铭树在合作商店每月20元工资。上世纪50年代。我和妹妹、大弟都在读书,沉重的负担使生活难以为继。好在母亲能说能干,当家理事一把好手,虽然没有文化,但通情达理,待人处事有见地,左邻右舍很佩服。
除了承揽全家的家务外,还学会补伞、补水鞋、养猪、种菜,帮人带小孩每月可挣5元、帮人洗衣服每月1元,通过她的勤俭持家,全家平安度过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大灾荒。母亲不仅操持全家,而且凭她的智慧,巧妙地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风险和灾难。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弟九发刚满8岁(小学二年级还未读完),去学篾匠,管吃每月还有八九元的收入,这样也减轻了全家的负担。每当我看到他幼小的身躯在师傅面前拉着篾片艰难地行走时,心里十分难受。那时我正在读初中,母亲为了让我升学,将这么小的弟弟送去挣钱,也是生活所迫。有一次。弟弟挨了师傅的打,而且打病了,我气愤地跑到店里找师傅评理,但那有什么用呢?徒弟挨师傅的打骂,是家常便饭。家境的贫困,加上父亲的懦弱,我们在小镇上被人瞧不起,连名字都被别人取了难听的绰号,我的名字是“炎生”,小名叫“炎仔”,可是被外号“糕仔”(“糕仔”即食用的糕饼)取代了,直到入伍提干后,回到家乡乡亲们才恢复了叫我“炎仔”。时常被人讥笑加耻笑,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刻上了屈辱的烙印。俗话说:丈夫有钱妻子贵,父母有钱子女贵。寒苦家庭的子女就像野外的小草任凭风吹雨打,全凭顽强的生命力挺立着。
1956年,小弟弟出世了,此时家境更为艰难,父亲将每月20元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当家,自己一分不剩。母亲白天累了一整天,晚上又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实在太困了,就打个盹,醒来再做,不到12点以后不休息。凌晨4点左右,听鸡打鸣,又开始第二天的家务。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他的零花钱就靠自己每月的尿钱(一桶尿卖5角钱)。父亲买不起烟,就要我去茶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捡烟蒂。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昨晚工商联开了会,快去捡些烟蒂来。我只好赶快跑到那里,将捡到的烟蒂交给父亲,父亲如获至宝,将烟蒂纸撕开,把烟丝包好,然后弄一点装到水烟壶上,点上火,在烟嘴上吸起来。烟壶里发出一阵阵响声。看到父亲这副嗜烟如命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我这辈子也不抽烟。说到做到,到如今我也没有学会抽烟,朋友有时就是递熊猫牌香烟。我也谢绝不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