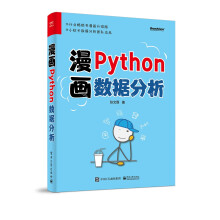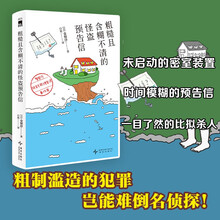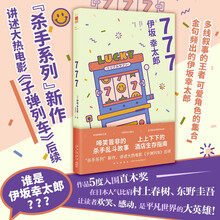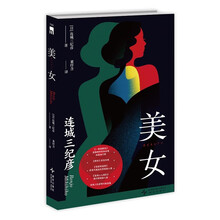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显示出了这种遥想在80年代后期以降的中国的普遍性。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近四十年后被人们再度“忆”起,与其说是一次本土发掘,毋宁说要归功于一种渐次内移为中心的外缘“断定”,真正被心悦诚服地迎归的,既非一位4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的精魂,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外观点”,而是后冷战语境中的不战而胜的冷战胜利者的权威定见。如戴锦华所指出,“冷战年代,张爱玲在不同脉络、版本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名与匿名,首先是特定的政治动因,并非她的全盛期的作品与文学成就,而是她江郎才尽之作:《秧歌》、《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获得命名之讳莫如深又心照不宣的现实驱力。在冷战分界线的彼岸,这一姿态令张爱玲洗脱了通俗与沦陷区写作的双重‘污点’,于海外中国学、准确地说,是美国中国学——作为美国冷战学科的‘区域研究’之现代文学史上脱颖而出。当同样的趋动,使得张爱玲于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踪影全无,成了并非惟一的文化失踪者与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天窗’之时,张爱玲则在依冷战逻辑全面蒸发、几乎成为绝对空白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放大凸显”,而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文化人对张爱玲的“钩沉”和经典化,则不但“显影了美国中国学至文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学术回流”,而且“含蓄且昭彰地成就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份‘告别革命’的选择与姿态”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