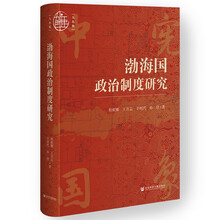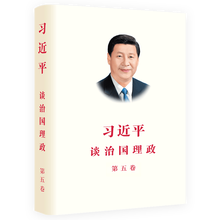第一章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剖析中国战略的理论框架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融人世界体系,期间恰逢新一波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昔日落后地区的崛起,中国先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继而成为世界转型的促进者。鉴于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崛起的历程,以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为核心特征的世界转型对中国影响巨大,构成中国制定和实施开放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构成中国战略框架的核心影响要素,而构建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成为中国全面开放的基本诉求。
本章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剖析,勾勒开放战略影响发展中大国的基本脉络,为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和优化提供理论基础。
一、世界转型: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
世界因文化交流而相连,因经贸往来而渐成一体。世界各地的联系古已有之,而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动因和标志,开启了创建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民族国家体制,标志着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
欧洲素有海外扩张的传统,加上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发生,欧洲在国际体系建构上拔得头筹。尤其是,1815年维也纳体系确认了欧洲大国间的均势原则,欧陆和平得以恢复和维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海外殖民扩张成为欧洲主要大国的首要战略选择。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后果之一是,“一个完整的军事一政治国际体系延伸到全世界……地理上的封闭消除了”。欧洲主导的新旧国际体系交替往往通过战争方式实现,维也纳体系历经和平演变,到20世纪初演化为两大军事同盟的对峙、对抗,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得欧洲之外的大国美国进入国际政治的核心,处于欧洲政治边缘的苏俄走向强盛。大战之后建立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显然是过渡性的,埋下了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火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大陆以惨烈的方式退出国际政治中心,苏美争霸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新主题。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具有两极对抗的意义,冷战而非热战的性质却赋予昔日殖民地联合自强的机遇,并为两极体系的和平终结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另一个新特点是,地区一体化成为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新潮流,昔日的国际政治中心西欧再次拔得头筹,并成为带动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昔日殖民地带发展迅速,发展中国家成为带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新力量中心,尤其是亚洲崛起似乎预示着由非殖民化开始的主导力量从西方的转移,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议题。冷战结束是第一次以非战争方式完成的国际体系转型,开启了从两极对抗走向多极互动体系的进程,是世界转型深化的集中表现,并彰显出历史性变革的深刻意义。
当今世界转型期主要表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所谓权力转移(Power Shift),即行为体及其权力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深入,自力更生不再被视为国家唯一的选择,地区一体化、互利共赢成为发展主流,融人地区合作被视为大国必然的战略选择,地区主义因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有鉴于此,经济和技术日益取代政治、战争和安全在国际制度的形成中扮演主导性角色。对所有国家而言,自由贸易成为双赢博弈,地区内贸易比重也随即增加,因为自由贸易使得各国可以通过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经济的规模效益,从而促成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权力转移速度的加速,不仅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永恒性地受到重视,技术、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因素也越来越被视为核心要素。大规模的权力转移带来了国家兴衰,促使国家集团化的发展、国际制度及其刚性的展现,并造就了国家行为体实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升的趋势,从而为全球治理开辟出广阔的天地。
首先,从国家兴衰的角度看,美国是权力转移新时代的最大获益者,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等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独占鳌头,是有史以来唯一集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技术霸权、经济霸权、文化霸权、人才吸纳中心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霸权。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一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是权力转移另外的重要受益者。它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经济基础和发展经验,并具有见微知著的战略眼界,可以及时把握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潮流,并紧跟美国之后。新型工业化国家大多是这场信息技术革命的积极跟进者,俄罗斯(因苏联解体而)先衰后兴几乎成为了权力转移的一种见证,而中国等崛起大国的风采更是举世瞩目,甚至西方有的学者预测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将共同崛起,呼吁世界与“金砖四国”(BRICs)齐飞。当然,权力转移不仅有受益者,亦必然有受损者,某些国家的处境甚至愈加恶化,沦落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成为当前世界需要迫切关注的重要难题。
其次,从国家集团化的角度看,国家集团化既是权力转移的来源,也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国家集团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趋势,意识形态对垒导致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主导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如火如茶的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了处于夹缝中的昔日殖民地走向团结,某些地区政治集团(如非洲、拉美)初步成型。这种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由欧洲联合带动的区域经济集团浪潮,地区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家集团发展的依托,其间北美、西欧、东亚逐步走向三足鼎立。美国也是地区集团化的先行者,早在19世纪之初,美国就通过“门罗主义”宣告了美洲体系观念的重要价值, 这一观念的当前发展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创建和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此外,作为在全球拥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大国,美国还积极介入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欧和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缘环境,确立了立足北美、覆盖南北美、面向亚太的战略。欧洲联合的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汹涌澎湃,欧洲联盟发展成为当前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组织,并逐步将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亚洲的集团化集中表现为东盟(ASEAN)的建立与发展,而中国嵋起及其与东亚其他国家共同走向繁荣的战略趋向在21世纪之初汇成了促进东亚一体化的潮流,开放地区主义逐步成为建设东亚一体化的共识。地区经济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性权力转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
其三,从国际制度的角度看,与此前相较,20世纪堪称国际组织的世纪。受到美国追求、确保霸权的战略谋划和全球化潮流的推动,国际组织在各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均有了重大发展,并逐渐成为各国解决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原则、程序和规范越来越成为大国推行其战略利益和小国维持其基本利益的工具,其制度刚性由此而进一步展现出来。例如,美国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但其对外军事行动每每积极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甚至不惜屡败屡战;冷战结束以来,政治性国际组织在监督国家选举方面的权威性逐步展现出来,不仅联合国监督选举的权威性得到重视,某些地区组织在本地区的选举监督也被视为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标志,如美洲国家组织(OAS)曾在4年间监督了11个拉美国家的大选;从经贸的角度看,WTO积极介入各国的贸易纷争,它所扮演的调解和仲裁角色受到诸大国的肯定。冷战后出现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国际制度的战略约束。与此相关,多边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战略意义得到多重视,多边协调开始被视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之一。
其四,从国家一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角度看,国家的传统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尤其是,政治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从两个方向对通常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传统国家权力进行分流:首先是纵向的权力分流,即国家权力的分层化,表现在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分权,以及越来越多的权力开始从民族国家向跨国家、超国家的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转移,传统的国家权力开始明显地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化;其次是横向的权力分流,即国家权力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原来垄断的一些国家权力开始向公民社会过渡。杰西卡。马休斯(Jessica Mathews)就此指出,国家行为体权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上升的最重要的引擎是计算机和通信革命,技术打破了政府对大规模信息收集和管理的垄断,信息技术也改变了人们对社群的概念,打破了等级制度,使得更多民众、群体共享权力的分散。
冷战的结束不仅带来了国家间的关系调整,还带来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国家政府不仅丧失了自主权,还要与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公共舆论迫使它们更经常地遵循特定的规范。今天,越来越经常的是,政府仅仅表面上拥有制定规则的自由选择,市场自己决定了事实上的规则。政府可以违背市场规则,但因此遭受的惩罚也可能是严重的。在这个加速变革的时代,非政府组织更迅捷地应对新要求和新机遇。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继续发展,非政府组织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跨越国界的行动。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展示权力的意愿,“9·11事件”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影响,其后国际社会采取的行动也进一步展示了多边外交、跨国协调的重要价值。
权力转移导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转移(Problem Shift),也导致国家战略的必然调整,生存不再是国家唯一的关注核心,发展和繁荣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首先,全球性问题激增,国际议程愈加丰富。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毒品交易、偷渡、国际难民、跨国洗钱、卫生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各类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与各国利益相关,通过单边方式难以彻底解决。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各国进一步依赖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使得国内国外界限相互渗透、日趋模糊,导致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传统分割不复存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促使各国不仅追求各自的利益,也更加关注整体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它不仅加强了国际社会的整体意识,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形成了一种战略约束,从而对传统战略观念和战略选择提出了挑战。鉴于不可能有一种战略能够解决所有全球性问题,理解世界转型成为各国制定战略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安全概念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上升为国际议程的主导因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是安全合作之源。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
安全观念的泛化意味着,传统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模式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得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应对非传统安全需要国际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
全球化无疑也是冲突之源。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全球化已经把经济和技术力量扩散于世界各地,而经济和技术的复杂性正处于超越当代政治控制能力的危险之中。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都会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产生脱节和紧张状态。”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它所引致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对人类发展的新挑战,某些传统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也需要我们倍加重视。
这些挑战更引起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9·11事件”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力量的上升与宗教恐怖主义实力的增长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两个互为因果的共生现象。鉴于美国过于强大,被列入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可能越来越容
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将其面临的主要障碍或危及生存的最严峻威胁归结为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并无失当之处,且集中体现了美国居安思危的敏锐战略意识。美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因素,作为其标志的是,一个国家将非国家角色作为头号敌人,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三。国家兴衰出现加速迹象。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兴衰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国家兴衰的进程甚至有所加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美两国同时取得巨大发展所造就的国际格局变革。
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根据大国兴衰规律探究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着力为之的。然而,令学者们始料不及的是,苏联解体与俄罗斯颓然衰落,使得世界权力分配进一步有利于美国,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甚至说,世界已经进入了美国独霸的时代。法国神学家弗朗西斯.费内隆(Francis Fenelon)曾指出,不能指望一个拥有超凡权力的国家长期保持彬彬有礼、举止有度。确实,强大国家的自然倾向决定了美国的预期和战略利益。21世纪初,美国由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变成谋求改变现存秩序的“革命者”。
美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中关于安全事务的安排没有正确反映当今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希望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包括同盟安排不能适应冷战后安全威胁的变化,不能满足世界安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需求。美国提出主权过时论、新干涉主义、失败国家论等新思想,以及先发制人、任务决定联盟等观念变革,采取了改造现有国际制度的种种单边主义措施,致力于创建新的国际规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单边主义并不是“9·11事件”、布什施政和新保守派阴谋策划的副产品,而应被视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至高地位后的必然结果。
美国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乃至抵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美国能够对重要的国际行动行使否决权,但不能决定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在今天单极一多极世界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是其他主要强国的威胁”。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就此警告说,美国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巨人。
中国崛起是世界性的重大议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开放和战略崛起为标志,中国国家实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人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进一步融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之中,积极提供地区公共物品。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和中国的东亚崛起这一结构性碰撞是否会成为一场新大战的起源?抑或中美可以通过战略接触与政策协调实现共存共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