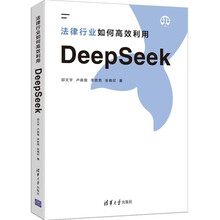但是,哈特的这个例子本身也是有重大缺陷的。事实上,在任何理论论证过程中,试图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说明理论的做法本身就有损理论之融贯性和一致性,甚至有损理论本身的彻底性。投毒者例子如果仅仅用来分析和颠覆“内在道德”的道德性的话,倒还有一定依据,但这种说明方式必然意味着对目的的考量,也就是说,哈特就得凭此说明富勒的道德性仅仅是追求“效率”而已,以便推翻富勒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紧密结合的判断。但这显然不是富勒的意思,富勒眼中的内在道德显然要实现,而且能够实现效率之外的其他正当目标。结果富勒也正是抓住所谓的“效率”批判,而对自己进行了充分的辩解。在这方面,富勒倒显示出坚持法律之“规则性”的彻底性。因此哈特其实完全可以不必举出一个投毒者例子,这反而损害了他的表达。
所以,与哈特对规则的分析完全相对,富勒坚持并强调自己秉持的立场,并以此立场批判哈特的实证主义缺乏目的考量。他说:“所以当我们说‘法律的道德中立’时,我们不能指法律制度的存在及其认真尽责的管理与人生事务中道德目标的实现无关。如果对法制原则的尊重对于促成这样的法律制度是必要的,那么当然可以正常地说那些原则构成了立法者和法律实施者的特殊的职业(身份)道德(morality of role)。”①富勒一方面表明对法制原则的尊重乃是实现道德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指明立法者和法律实施者在维护这种道德时所承担的责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