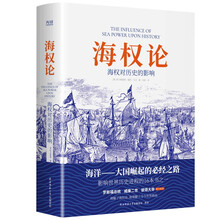三‘、哲人与立法之言
只是在城邦之内,在为城墙所环绕的那一块空地之间,公民的言行才具有了这种意义。城邦是公民言行的舞台,换言之,公民之言的出现是后于城邦的建立的,它的内容不可能涉及城墙本身,即不可能涉及建立城邦的活动。但是,城邦从何而来?当然不可能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言行”建立的。因为此时尚没有公民的言行,只有已经有了城邦,有了为城墙所环绕的空间,才有公民的行动。
这一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性。任何一种政治生活形式都面临解释它的合法来源的困境,因为政治生活形式本身总是先于“合法”观念的出现。具体地说,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可能自己建立起使这一法律制度成为合法的前提,换言之,任何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都不能来自于自我叙述,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也不可能制造自己立足的地面。当一种政治生活形式谈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时,它的这种“谈”只能是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回忆。回忆是一种留恋,留恋开创行动所迸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必然始终处于衰竭过程之中,衰弱得愈厉害,留恋也就愈强烈)。
政体(生活方式)的悖论在于:“合法”只有在既定的制度法律框架之内才是有意义的,它是后者的产物,因此这种“合法”是不能反身运用于对于政体的辩护的。由于这一悖论的存在,假设一种外在(近代以来是内在的)力量的存在就非常必要。这种力量可以不受政体的限制(具有超越性或内在性),并导致了政体的创造,它是政体合法性的源泉。任何一种政体形式,只要它试图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能不顾及它的起源,它必须持续地从它的起源中汲取合法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