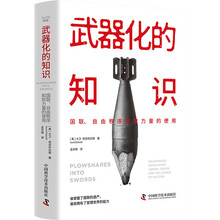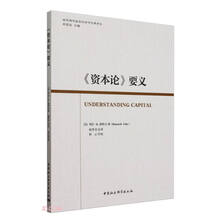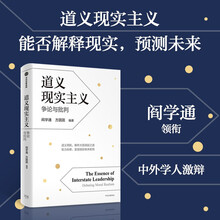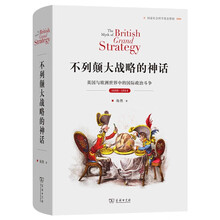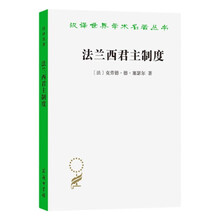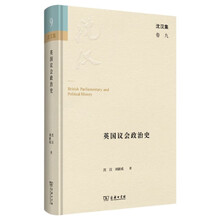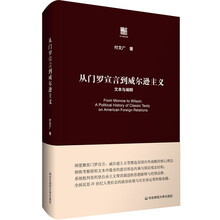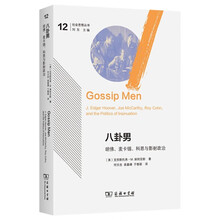人们必须重新思考欧洲模式。这一模式已经运转了50年之久,今天却不再有效。不仅如此,随着欧盟的东扩,一个新的时代,即边界推移和边界消失的合作时代,也开始了。这难道值得奇怪吗?欧洲化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迄今为止,它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欧洲的兴奋之情(或许还有怀疑),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直到今天仍然未被理解,未被接受。这种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的跨国家、跨社会共同体的构成形式,超越了一切现存的范畴和构想。欧洲的范例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政治概念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离历史现实已多么遥远,已经变得多么迟钝——它们仍然被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思维大厦和方法论之中。
究竟是什么把一个幅员更加辽阔的欧洲维系在一起的?显然,是一种新的构想,世界主义欧洲的构想!这本书所要阐明的正是欧盟的崭新构成方式和论证基础,此外还要提供并展开一个概念——“世界主义欧洲”的概念。同时,此书也是一种在反思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理解欧洲化,并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其重新加以定位的尝试。
本书在分析当今欧洲社会面临的矛盾、风险的基础上,构想了欧洲的世界主义化战略。全书围绕着欧洲社会的国家形式、可变边界、社会风险、外部矛盾等重大命题进行思辨和论述,提出了世界主义的理论原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