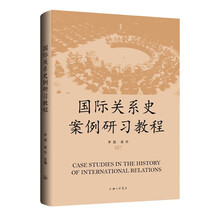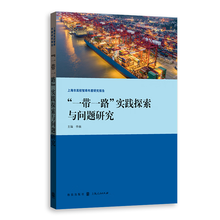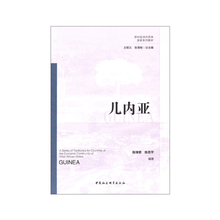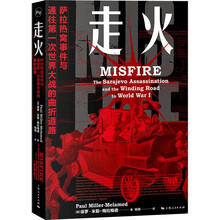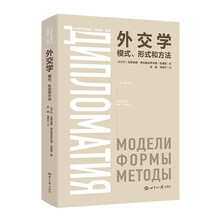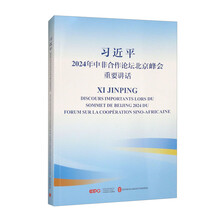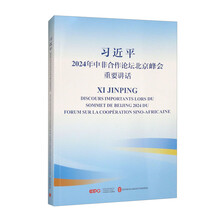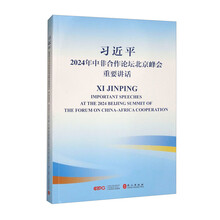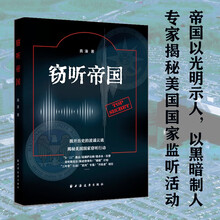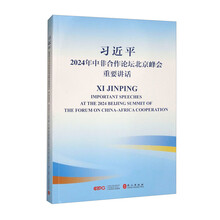在当时美台相互间的心理认知结构中,美国决策层对台湾的心理认知形成“皮格玛丽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制约着国民党政权的演进轨迹,使台湾当局向着美国期望的方向演变;而台湾当局对美国既依赖又防范的心理发育成“怨妇心态”;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美国对台政策。
美台结盟之前,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已有长期的交往。在抗日战争后期经宋美龄等人成功的外交活动,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形成较为正面的印象,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民主的、亲西方的和反共的政权,将会成为二战后支撑美国主导的亚洲霸权秩序的主要支柱。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认知形成一种“晕轮效应”(Halo Effect),进而形成心理定势。虽然美国政府自杜鲁门时代起对国民党当局的无能与腐败早有认识,但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懈地积极反共的立场仍然巩固了这种“晕轮效应”的心理定势。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决策者殷切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实现台湾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能够成为落后地区凭借美援实现经济起飞的典范,能够在海峡两岸追求现代化的竞赛中获取胜利,成为展示西方模式相对于共产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橱窗。为达到此目的,同时也是为了促使国民党安心海岛建设,打消“反攻大陆”的念头,美国决策层还希望国民党当局裁军缩编,重塑军队结构。美国凭借自身在美台非对称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及美台间的定期沟通的机制,将自身对台湾政权的期待之情持续而清晰地传递至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导着国民党的决策,使国民党乃至台湾社会都向着美国设定的方向演进,从而形成“皮格玛丽翁”效应。而国民党由于在美台非对称结构中处于弱势,再加上内战末期曾遭遇美国的厌弃,因而对美国形成了既依赖和感谢、又怨愤而防范的矛盾心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