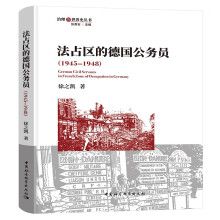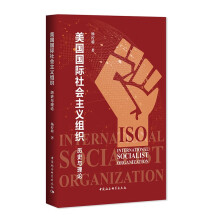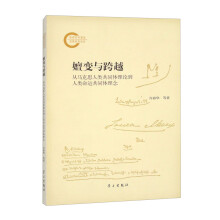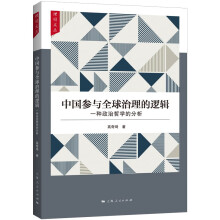第一章 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
20世纪是一个有着大量幻想的年代,这些幻想由那些怀有轻率梦想的理论家们所设计,企图使历史按他们的意志发展。最终,巨大的法两斯主义的野心不仅仅制造了乌托邦,也产生了奥斯威辛和古拉格集中营。现代人试图以他自己设计的一个上帝来替代失去信任的真正上帝,这种努力的结果却只是产生了大屠杀和灾难。傲慢的同伙是灾难。如果应该从1914到1989年的血污年代中吸取一种教训的话,无疑就是这了。
美国人为摧毁这些假上帝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一过程中,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来的美国政策的各个设计者,保持着他们自己那令人兴奋的梦想,几乎不比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真正追随者们的野心逊色,在精神上他们是相似的。
客观形势凑在一起,制约了20世纪美国的理论家们。对于威尔逊来说,有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一个坚决反对“忍受不愉快事情”的参议院。总统明确要求参议院通过巴黎谈判所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参议院的反应则是完全拒绝了这个条约。结果,作为威尔逊世界和平设想核心的国际联盟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建立。对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个威尔逊的继承者来说,他对公众在长达多年的萧条继而战争之后对常态的渴望,有着精明政治家的敏锐感觉。他建立一个新联盟——联合国——的蓝图,非但没有使世界事务革命化,而是使其他国家满意于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均势。对于约翰·F·肯尼迪来说,可能在口才上跟威尔逊一样雄辩,他的限制来自于一个核武装的对手。结果,肯尼迪简短政府的特点,不是成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想主义,而是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是威尔逊之后第一位身居白宫的南方人,越南战争使他通过新政来改变湄公河流域人民生活的激进计划匆匆了事。对于吉米·卡特来说,他在宗教热情上与威尔逊一样,不合时机但又必然要面对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实,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核裁军只有待以来日。正如此,现实一次次地阻碍了威尔逊主义者的热情。
阻碍,但不是推翻。尽管威尔逊自己表示作为政治家的失败,也尽管他的继承者们在按威尔逊的期望重新塑造世界方面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但威尔逊的范式——作为一种世界观,也作为规划和表达国家目标的基础——给美国的治国方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注意到的,“自从威尔逊转折性的总统任职之后,美国对外政策便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鼓点声中前进,并一直行进到今天”。
威尔逊理想的要素是什么呢?其核心是试图按照美国的想象来进行一种世界性的重新改造,从而达到永久和平。这在威尔逊最初表达出这一设想的时候就是真实的,直到今天它依然真实。
威尔逊本人的目标,如他著名地所宣称的,便是通过消除产生战争的所有条件来“结束所有战争”。威尔逊希望扔弃旧世界对相互竞争性国家之间敌对状态的依赖,重新建立起一个国家共同体。威尔逊相信,这样一个共同体,在美国的赞助之下,在新世界早已在发展之中。这方面,当时存在的泛美联盟,即今天美洲国家组织的先驱,便提供了这样一种适于世界范围内实施的模型。但是,尽管名义k是一个平等的共同体,泛美体系实际上二却并非如此。它的存在促进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并使之永久化。
在1917年1月向美国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也是绕过外国政府首脑径直向全世界人民的一次宣讲中,威尔逊清楚地说明了他提议的新外交的详情。他概略地叙述了一年后提出的“十四点”的初步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海上自由,经济开放,裁军,不干涉(内政),以及以“协同和平的契约”来代替均势——威尔逊提出的这些术语,不仅仅是为结束正在进行中的欧洲冲突,而且是为了使战争本身永远过时。接受这一方案,将会出现一个主权国家为自由民主原则和自由事业全力以赴的世界。也就是说,致力于这个意在使美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正如威尔逊在其演讲的结尾向国会担保的那样,“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会代表任何其他人”。而事实上他的结束语是,“它们是人类的原则,必须取得胜利”。
上帝本人愿意全世界都来热诚地接受美国的原则。对此,总统是深信不疑的。这种深信——对历史,也对美国在将历史引入其预定目的地中的角色——是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信念。这信念是不断展开的戏剧性事件的中心,而剧情将要从到目前为止尚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美国介入欧洲僵持的战争。实际上,就威尔逊本人来说,他怀有对军备、军国主义、杀戮的深深厌恶,只有从他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他是以上帝的使者去行动,深信美国的使命是神意使然,才可以解释他在1917年春天作出的介入欧洲战争的决定。美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也是巨大的:这就是“使世界本身最终变得自由”。3只有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业才能使威尔逊有权将年轻的美国人派到西部战线的“屠宰场”——这是对旧世界到底背离上帝安排多远的一个最极端的表达。对威尔逊而言,他反映了一种长期的而且此时依然强劲的美国传统,即诉诸武力对于美国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出于私利,武力是一种勉强使用的临时措施,而不是一种国家性格的持久表现。
我们今天见到了威尔逊式的野心和威尔逊式的信念的复活,然而现在它们却与一种对武力的明显热情结合在一起。随着冷战的结束,曾一度使美国理论家们受到制约的因素消失了。同时,美国全方位史无前例的军事优势——这是冷战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希望,就是这种军事优势终于是使美国能够履行其天定使命的工具了。
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威尔逊的真正信徒,发起了这样一场复兴,为美国再一次强调了“重新开始(改造)世界的力量”。在90年代,比尔·克林顿,受里根成功地对抗苏联的熏陶,在美国选民的支持下,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在感觉到美国代表了“历史的正确一方”后,克林顿强调,没有什么可代替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国设想的全球化世界了。尽管知识分子仍在继续争吵“历史的终结”,亦即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否真的即将到来,美国总统则对这一还在讨论的问题作出了断言:历史已经说明了它提供的答案是可靠的。几乎没有总统的政治对手去挑战他对历史的解读,虽然在其他方面他们轻视克林顿以及他所倡导的一切。正如自由派一样,保守派也同样拥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民主资本主义对其他一切主义的胜利是不言而喻和不可逆转的。
在现今的十年中,在2001年9月11曰的灾难性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他在候选人的时候曾许诺要恢复美国政策的谦逊品质——终于露出本色,在他的追随者看来已成为“威尔逊本人之后最威尔逊式的总统”。5这样一个布什,一个具有有限的历史知识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智商的骄傲,对带有“国家建设”之意的任何事情都公开表示反感,倒是以如此快速和明显的激情注意到威尔逊的原则。这只是威尔逊原则如此深刻地进入到全体美国人的精神当中的一种迹象。对布什来说,就像威尔逊一样,美国人的使命感和上帝的意志都是自明的。“美国的理想便是所有人类的希望”,他在“9·1 1”事件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此宣称,指望通过这种源于《圣经》的比喻来推动他的国内纲领。“这希望仍旧照亮了前面的道路”,他继续说道,“亮光在黑暗中闪耀,但是黑暗不可能战胜它”。
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后一年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力证实了这种威尔逊主义的复兴。在总统为这篇报告写的序言中,他宣布20世纪最大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后果。在20世纪中,自由击败了集权主义。这一历史的直接后果是永远地确认了存在着“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在刚刚开始的这个世纪里,任何国家如果拒不遵从这一模式——美国体现的范式——便注定要失败。只要人类抓住机会,自由之最终的和无法改变的胜利——“关于人类尊严的不可谈判的要求、每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便会向我们走近。按布什所说,“在这一巨大使命中进行领导”,这仍旧是美国的责任。
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他在“9·11”后其他的大批宣言(常常穿插着总统对上帝意图的领悟)给一些观察家们以出奇地专横跋扈的深刻印象。专横跋扈还可论证,但绝不出奇。正如亨利·基辛格l994年所观察到的,“每当美国面临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务的时候,它无论如何得回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上去”。2001年9月11日的令人震惊事件挑战布什当局去建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新秩序,它本能地转向威尔逊。实际上,布什当局的反应说明这次对世贸中心以及五角大楼史无前例的攻击对支撑美国对外政策的设想的影响是多么小。恐怖主义袭击只是在恢复天命召唤美国这样一个真正的世界性民族,按美国的标准去建设一种普世性文明的信念上取得了成功。“美国没有因为‘9·11’事件而改变”,罗伯特·卡根正确地评论道,“它只是变得更为本色了”。美国人更加本色了,他们坚持他们不仅仅“在过去的十年,而且在过去60年的大半时间里,或者有人可能甚至会说,是在过去四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从事的事业。按卡根所说,这一事业的目标从一开始便是控制权:“客观事实是,美国人甚至在他们建立其自己的独立国家以前,便以日益扩展的弧线来一直向外扩张他们的权力和影响。”
概言之,当提到目标时,在弥漫于这一新威尔逊主义时期的思想中,几乎没有思想称得上真正新的东西。无论是否将这种复兴归功于里根、克林顿,以及小布什——或者,作为另一种选择,也许更为恰当,归功于共产主义的崩溃、20世纪90年代虚假的新经济,以及基地组织的出现——这种世纪末威尔逊主义的复兴都仅仅是代表着过去这个世纪大多数时间内美国政治家们一再坚持的意识形态权利的全面开花结果。
但是,今天的美国人旨在达到那些目标的手段则是新的,也值得更大的注意。关键是,冷战结束之际,美国人支持军事力量。实际上,对武器和军队的怀疑论,弥漫于威尔逊原初的设想中,甚至是遍及于美国从建国以来的试验过程中,然而现在消失了。政治领导人,自由派和保守派一样,都迷恋于军事力量。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一种缺少考虑的盖茨比式的激情。这是一种全然不顾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激情。几乎没有掌权者公开考虑过,不管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还是为了达到永久性的全球军事优势地位,重视军事力量是否与美国原则一致。实际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人朝着军国主义方向的偏离是因为缺少来自真正有声望的政治人物的异议。政治阶层的成员们,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要么是没有注意到某种重要的东西可能在酝酿之中的可能性,要么是选择了拒绝注视这种征兆。
不妨将这与较早以前美国军事历史上的转折点比较一下。当l917年美国投入到欧洲战争中去的时候,参议员罗伯特·M·拉福莱特,一个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坚定的进步主义者,警告美国人“有人正借口将民主带到世界其他地区”,伍德罗·威尔逊实际上所做的“更多地是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和摧毁,这种破坏和摧毁高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一代人时间内去修复它的可能性”。20年后,当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法使这个国家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坚定保守派,雄辩地证明了可能导致的结果。他在1941年5月17日演讲中说道,如果美国保卫旧世界的小国更甚于保卫它自身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在德国和全欧洲永久地维持警察力量”。正如塔夫脱看到的,这不是美国的适宜角色。“坦率地说,美国人民不想统治世界”,他说,“我们也没有对此作好准备。这种帝国主义完全与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的理想不相容。它不是我们的天定命运,也不是我们的国家命运”。拉福莱特和塔夫脱都不是唯一的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声音。
这里的目的不是说,在他们的时代,拉福莱特和塔夫脱使形势完全步入正轨。他们没有,尽管这些事情表明他们比威尔逊或者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更加有先见之明——这两位总统都曾预言战争之后永久和平将会到来。这里的目的在于说,在那些日子里,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一种令人清醒的认知,认为战争本质上是恶毒的,会引起各种成问题的后果,军事力量是民主政治需要小心谨慎对待的某种东西。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敏感性几乎全部消失。当提到军事问题的时候,国家政治舞台上没有反对的声音,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最不满意现存政策的人。
例如,当参议员约翰·克里,这位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在2004年进行总统角逐时,他说他与乔治·W·布什国家安全政策的差异是策略上的,而不是在优先原则上的差异。克里并没有质疑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将是几代人长的“全球反恐战争”这种说法是否明智。引起克里愤怒的不是这种无限期战争的前景,而是战争“管理极其不善且难以为继”。克里指责布什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缺少“使他们能尽可能有效战斗所必要的准备和硬件”。布什指望太少的军队在太短的时间内去做太多的事情。克里宣布,“保持我们军队的强大并且尽可能保证我们军队安全,这应该是我们的最优先任务”,他许诺如果当选会改正这方面的缺陷。美国人能够预期到如果克里当选总统,他会去扩充武装部队,并且提升其战斗能力。
然而由此可以见到,克里的小心谨慎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正是该候选人的方法,意在表明他在防卫上是安全的,无意于离开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共识。
在这种共识的情况下,今天的主流政治家确定无疑地以为美国军事优势是一种绝对好事,是更大的美国优势地位的证据。他们把这种武装力量看成是创建一个与美国价值观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这一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共识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国政策的军事化,并且怂恿了这种(军事化的)趋势,表明美国社会本身目益迷恋于其军事力量举世无双的自我形象。
这种美国新军国主义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自己。首先是从范围、成本以及美国现今军事组织的结构上。
在美国历史的头两个世纪,华盛顿的政治领导入根据即将到来的安全任务来评估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能力。对国家安宁的严重和紧急威胁可能要求一个大而强的军事组织。在没有这样的威胁时,决策者相应地缩小军事组织的规模。随着危机逐渐过去,一俟危机消失便进行裁军。1865、1918、1945年都是如此。总的原则是维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武力,不用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