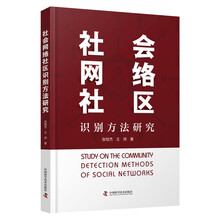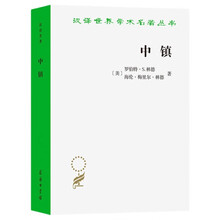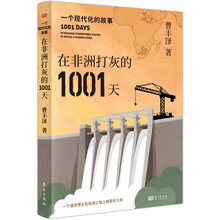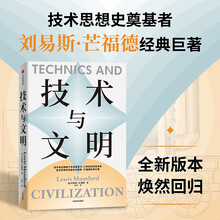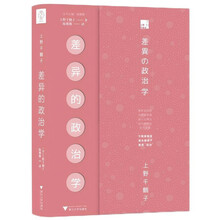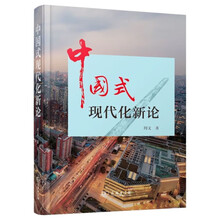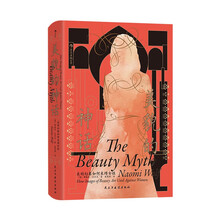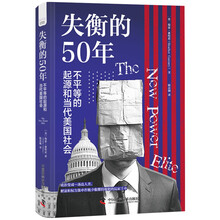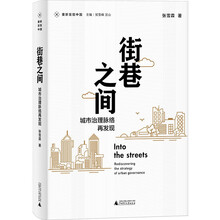缠足与放足<br> 1缠足的起源与发展<br> 缠足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缠足与放足的历史过程本身也透露出中国妇女生活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清代,缠足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区别的标志之一,我在研究清代的族群问题时发现,一般汉族以外的民族或族群,在说到他们与汉族的基本区别时,往往会提到汉族妇女的缠足,“他们的妇女是裹小脚的,而我们是没有这种现象的”,这类话语我在调查中常常会听到。<br> 缠足起于何时,历来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六朝说、唐代说、五代说。大体上每一种说法都是从前代的零星文献与诗词作品中,着意钩沉,每一种说法也都找到了一些根据,而每种说法的反对方也都找到了一些反对的论据。但大体上,此种风俗起于南唐而成于南宋,则为一般学者们所接受。<br> 说到缠足起因,大概说来有四个方面:审美的要求、汉族历史上两性隔离制度发展的结果、宋明理学的推动、处女嗜好的促进等潘洪钢:《汉族妇女缠足起因新解》,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0期。汉族人追求女子身材美感由来已久,古来就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历朝历代歌颂美女们身材姣好、步履轻盈的诗句不胜枚举,白居易晚年以他自己的两个小妾名字入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里用杨柳形容女性的身段,将古人欣赏女性身材姣好的审美观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大概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女性脚小更能展示身材,摇曳生姿。所以五代以前虽然妇女不缠足,却有不少歌颂小脚的诗。以女子娇弱、步履迟缓、摇曳生姿为高贵动人。缠足一出现,就受到很多文人的欢迎,它是长期以来人们审美倾向发展的结果。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文豪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菩萨蛮》词中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辛弃疾《菩萨蛮》有:“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句,常常为人们引用。林语堂先生曾描述过女子缠足后的步态:中国女子的缠足,完全地改变了女子的风采和步态,“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了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而正是这种“可怜的感觉”,膨胀了封建士大夫的自身优越感,从而滋生出其“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林语堂:《吾国吾民》,见《林语堂文集》第8卷,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br>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审美情趣,而汉族追求女子窈窕曼妙身姿的传统,就是女子缠足习俗形成的最原始的动因。相传,南唐李后主的宫中,有一个叫窅娘的宫人,她用白色的绢帛裹住自己的脚来跳舞,有回旋凌云之态,引起一片赞誉。此后,社会上出现模仿她的裹脚的风气。这种风气适应了汉族人的审美要求,逐渐开始推广开来,这便是缠足的由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定居农业发达的汉族很早就进入了男权社会,在私有制发展的情况下,男性为了保证财产的继承,必须有明确的属于自己的后代,因此产生了对女性行动的种种限制,周代以后就出现了对妇女的隔离制度的萌芽,即为保证妇女的贞洁,限制其与丈夫以外的男性的接触。贞洁观念是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念,此种观念在宋代以后发展到了极致,而缠足对妇女的外出行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刚好适应了这种要求,所以上层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推广此种习俗,对缠足在汉族中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宋明理学的促进、上层社会的倡导及汉族对于处女的要求,都成为缠足发展的推动因素。<br>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审美的要求是缠足现象最初产生的基本动因之一。由追求窈窕身材而转向使身姿“回旋有凌云之态”的小脚,进而转向“高度诡秘的”性心理,其间的轨迹是符合人类思维的逻辑的。到后世“三寸金莲”成为一条把精神的力量导入性领域的途径,成了男女情爱时的性感带,作为撩拨性情绪的源头,则是一种与当时文化环境相呼应的性刺激方式。至于妓鞋行觞,以三寸金莲载酒行令,如同清人袁枚《答人求妾书》中说的,“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就多少有些变态了。那种认为缠足起初就是为满足男人们变态的性心理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那是后来才有的事。<br> 明代,对妇女贞洁的要求发展到极致,妇女缠足成为汉族最普遍的习俗。清入关前,皇太极就曾下令,不准学习关内妇女缠足之习。入关后,顺治二年即下令,以严禁女子缠足并试图改变汉族妇女缠足之风。顺治到康熙时期,清廷曾多次发布禁令,不许妇女缠足,但汉民族强大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而清廷对风俗的此种干预也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极大反感。康熙七年(1668),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建议弛缠足之禁,王认为:康熙三年所定禁止缠足的法令,规定康熙元年以前所生女子缠足不再追究,元年以后生女,严禁缠足。违者严处,其父有官职者交吏兵二部处置,系平民则交刑部责打四十大板,并处“流徙十年”;家长有失察者,枷号一月,责四十板,官员失察,也要交吏部等部门处理。此种规定太过严厉,造成民间诬妄举报,牵连无辜。王的建议得到批准,“裹足自此弛”(清)钱泳:《履园丛话·杂忆》卷2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1页。。此后,清廷虽然也时有颁布新法,禁止缠足,但在实际执行中,未再对汉族妇女的小脚认真干预,只是严令旗人妇女不得缠足。但流风所至,习俗难改,且旗人中也逐渐出现了个别缠足的现象,此种现象在嘉庆时遭到多次申斥。历史记载中就有旗籍女子用细布把脚裹成条状的,称为“刀条儿”脚,因为成年女子无法将脚裹成小脚,所以才有了这种办法。汉军旗人中的缠足现象更是难以禁绝,如广州的汉军旗人就长期保持了妇女缠足的习俗。不仅如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其实旗人妇女的马蹄底鞋,也与汉族妇女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妙,旗下妇女穿上这种古式的高跟鞋,既有汉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浸染影响,也有追踪社会时尚的心理原因。<br>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明确把裹足变成了高贵妇人专有的装饰,而对贱民阶级的女子,政府以法令禁止其实行。清代实际社会生活中,继承明以来的风俗,缠足成为女子身份高贵的象征,为上层社会所提倡,为普通人们所接受。女子裹足与男子读书一样,成为进入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普遍认为,女子小脚是高贵的象征,是素质高的表现。清代的一首《鼓儿词》这样说:“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衩女,为何脚步两样声?”缠了足的是小姐,不缠足的是丫头,也说明了缠足是女子尊贵的象征。女子缠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否找到一个好婆家,影响其成人以后的生活。河南安阳的歌谣云:“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为了使女儿长大后能找个好婆家,做父母的也要狠心地、不顾女儿痛苦地硬是给她缠小脚。民间素有“娇男不娇学,娇女不娇脚”之说,对于男孩子来讲,尽管读书很苦,但它是进入上流社会的基本途径,所以再苦也要读;同样,女子缠足虽然是一种苦难,却是身份的象征。尽管缠足简直就是一种残酷的肉刑,可是越是慈爱的父母,越不能娇任儿女。“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这个“肉刑”不管妇女是否接受,其所受的苦难是注定了的。<br> 清廷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清代却是缠足风俗最为流行的时期。全国除了两广地区和江苏、安徽、云南、贵州等省,“外此各省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流风所至,缠足成为妇女最为重要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品德的修养,如果一个女人是天足,则父母以为耻,夫家以为辱,甚至亲友乡邻传为笑谈,女子本人也自惭形秽,相沿成习。除了最贫困的劳动妇女外,一般小康人家的女子都自幼开始裹足。全国以陕西和山西妇女裹足最为有名,有“从来小脚说山西”之誉,山西则以大同名气最大。山西大同偏僻农村有所谓“晾脚会”和“赛脚会”的比赛,每年春秋两季,小脚妇女们梳妆打扮,聚集在街头,展示她们的小脚,让来往人等“品脚”,引以为荣。直隶宣化也有“小脚会”,每年五月十三日在城隍庙会上举行。这天是关羽诞辰日,庙会上百戏竞集,游人如织,妇女们“大率列座门前,多或十余人,少亦五六人”,频繁换鞋,引得路人注目,“游人指视,赞其纤小,则以为荣”。有诗说:“惹得游人偷眼看,裙边一样露纤纤。”缠足女子,脚多致残,不良于行,在缠足盛行地区,往往要拄拐杖,最典型的如陕西,女子被称为“三足”,指的就是当地女子“行路无时可离木杖也”。即使是缠足之风不甚流行的广东地区,富贵人家女子也要以缠足来显示其出身为“巨室”。与陕、晋等地不同,广东缠足,崇尚“短圆”,以足长二三寸,横向也只二三寸许。传说广东最上品的缠足,能站立于小碟子之内。所以离开了别人的扶持,一步也不能走。嘉、道时,浙江临平有一姚姓妇女,脚小到只有一片树叶的样子,平日做鞋累了,鞋帮和线一起插在头上,小到人们无法看见。姚美人的名声很大,“闻名乡里”,当地有个美人埭的地名,就是由这个女子得名的。但这个姚美人脚太小,行动不便,后来被她的儿媳欺负致死。<br> 缠足被视为富贵人家的象征,也是妇女品德的第一要务,风行草偃,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以清代的情况看,“实由富贵贫贱阶级之见深入人心”。《清稗类钞·容止类》。缠足也成为士人阶层普遍欣赏的事物,甚至也成了性的敏感区域,当时流行上品的缠足有“七字诀”,即:瘦、小、尖、弯、香、软、正。著名文人李渔认为最上品的莲足应该是“肥秀软”。有个叫方洵的文士写了《香莲品藻》的文章,专门研究小脚,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而风流文士们把酒狂欢时,以所谓“香莲”载酒,更是在酒酣耳热之时,于席间注入了性的联想与意会。<br> 清代不缠足的大体只有下层劳动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如我们前面提到广西有女子以抬轿子为职业的,如果是缠足则不可想象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