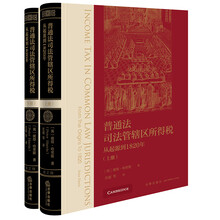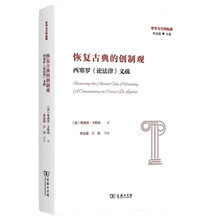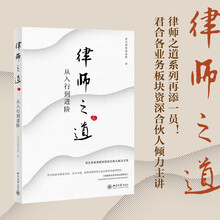施米特
价值的僭政(朱雁冰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院在解释波恩基本法时,未经审慎思考便诉诸价值逻辑。这当然并不是说,价值逻辑在我们这里取得了法理和法律的力量,它经由有约束力的专业技艺(verbindlicheStandeskunst),即德意志最高法院的法学,变成了德国法官制订的法律(judgemadelaw)。在这一方面,联邦共和国的立法者至少还持审慎态度。相反,肩负司法责任的法官们却需要为自己的判决和裁定提出客观根据,就此而言,今天有众多价值哲学供他们选择。问题是,这许多东西是否能够提供人们所希望的、普遍令人信服的客观根据。联邦共和国的某些法官也许觉得,自己是某些价值的先驱。然而,要让他们作为带有价值哲学标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力量、权力、目标和利益的先驱执行法律,他们似乎还有疑虑。这些法官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探求自己的价值逻辑的问题贬低为一场口水战。就实际观察的角度而言,这些法学家很快会感到,激烈交锋中最尖锐的对立在关键时刻变成了一场口水战。就理论反思的角度而言,这些法学家懂得法定效力(Rechtskraft)、法定财产(Rechtsgut)和法定价值(Rechtswert)之间的区别,不会将它们看成毫无意义的细微差别。这些法学家受过法学史教育,懂得财产首先是指东西本身(resmeaest[这是我的东西]),继之成为一种具体的“占有东西的权利”,而现在却消解为单纯的价值。
即便立法者拟定的法令一般都应为自由价值逻辑的活动空间划定可以测度的界线,立法者也可能在其官方语言中陷入众多价值哲学中的一种价值哲学的词汇中。例如“重订民法的人身和名誉保护法”草案的解释,开场第一句话就是:“在自由的民主制度之下,人的尊严是最高价值。它是不可侵犯的”。“它”——即价值,仍然是不确定的。
这样一种陈述方式也许表现出某种非常简单和现实的东西:一个多样的、即超多元主义的、由大量异质集团整合而成的社会,必须将与它相当的公众变成展示价值逻辑的演练场。于是,集团利益便以价值的形成出现:基本法律范畴变成了与之相当的某种价值体系的定位值(Steltenwerten)。价值的变化、即“价值化”(Ver-Wertung),使不可计算的变得可以计算了。如基督教各教会、各社会主义工会以及农场主、医生、遇难者、受难者、被驱逐者协会、多子女家庭等等完全不相干的财产、目的、理想和利益由此变得可以比较和达成谅解,以致可以计算出社会产品分配的比率。只要人们始终意识到价值概念独有的特殊性,并在其所从属的地方——即经济领域——寻求其具体内涵,这种作法便有积极意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