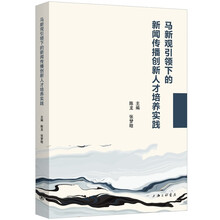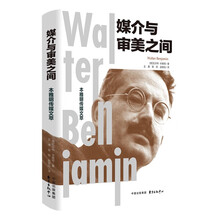第一章 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
不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哪一个领域,谣言无所不在。
谣言还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便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报纸和后来的无线电广播的问世,以及最后视听设备的急剧发展,都未能使谣言烟消云散。尽管有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仍继续以口传媒介的方式获取一部分信息。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从此以后,两者各有其流通的领地。
尽管如此,我们对谣言仍然不甚了了。对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研究却如此之少,实为罕见。谣言作为一个神秘乃至神奇的事物,至今依然是知识领域的真空地带,或者是人烟罕见的荒漠地区。
被称之为谣言的现象究竟始于何处又终于何方?它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口头传递有何区别?事实上,每当我们以为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总是溜之大吉。人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分辨谣言,但却无人能给谣言下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总之,如果说我们每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谣言的存在,那么我们却未能对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划定一个一致公认的精确的界线。
如何解释研究此题目的著作寥若晨星呢?第一条理由就是这项任务难乎其难。研究报纸、无线电广播或电视轻而易举,因为它们的资料都保存着。人人都能去查阅杂志或报纸的合订本。同样,录音机和录像机也使人们可以重听或重看过去的节目。而研究谣言却完全不同。除了少数例外,研究者在获悉谣言的存在时总是太晚:谣言要么已经过去,要么已进入最后阶段。于是研究者只能通过采访去追寻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谣言,而记忆容易遗漏、容易理性化和失真。这样进行工作,研究者实际上研究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然而记忆是很难供人观察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人们更注重于对谣言的道德分析,而忽略对谣言结构的分析。
一个令人尴尬的信息
首先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人民士气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很多研究小组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
他们是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呢?这个领域的两位奠基人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参考书目5]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而纳普[参考书目853]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彼得森和吉斯特[参考书目115]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是,谣言是一种“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这三种定义十分接近。这三种定义首先都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或某事一些新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谣言与传说不同,传说只与过去的某桩事实有关。其次,三种定义都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出于使人高兴或使人产生梦想便去传播谣言的,在这一点上,谣言与滑稽故事或童话泾渭分明。谣言竭力使人信服。
在对谣言下了定义之后,作者们便举出一系列的例子和试验。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举出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涉及“虚假的”谣言:公众曾一度相信的那些谣言其实毫无根据。然而有根有据的谣言并不罕见,如有关里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以及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乔治?蓬皮杜等人生病的传闻。每次货币贬值之前,总有谣言先导。在企业内部,谣言透露人员的解雇或调动。在政界,谣言总是比部长们的去职先行一步。另一个例子,1985年,在得到官方证实的几个星期之前,谣言就流传开来,宣告了法国工业的一大成就:美国人希望使用法国汤姆森无线电报总公司制造的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来装备其地面部队。果然,这一陆军流动通讯网系统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被采用了。
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任何真实性成分。他们没有一处说到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而只是提及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
于是。尽管煮识到谣言并不绝对是虚假的。似乎也必须竭尽全力去阻止这种表达方式。因此,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实际上只是介绍了“虚假的”谣言的情况。更有甚者,在读者对谣言的危险性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他们展示了谣言不可避免地走向错误的过程。他们的试验遐迩闻名:一个人在观看一张街景照片数秒钟之后,将他所见转述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如此类推。到了第六或第七个人获悉这一信息时,与开头的照片内容已相去甚远。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的试验企图证明,谣言只能走向错误:在流传过程中,无论从其本义还是转义上来说,谣言都离真实越来越远,反映的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于是求证完毕。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模拟试验与谣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并非完全吻合。有时,消息在流传过程中,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准确传递。
这些美国研究者在战争情报处供职,除了其他职责外,担负着控制谣言的消长起伏的任务,因此他们特别注重于使这种交流方式信誉扫地。既然谣言的概念是中性的,那么就必须仔细选择合适的例子来证明它的虚假性。然而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一个矛盾:既然谣言都是“虚假”的,又何必去担心它呢?根据经验,老百姓应该早就学会不信谣言了。
事实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在战争中,敌人和他们的耳报神——第五纵队——能够从谣言中获取某些隐匿的实情。这证明了谣言并非总是无稽之谈。
为了避免机密情报泄露,战争情报处到处张贴广告,告诫人们,要做一个好公民的话,就不要去传谣(“嘘,隔墙有耳”)。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劝告都忽略了一个主要问题:如何教会公众识别谣言?于是我们实际上又回到如何给谣言下定义的问题上来了。上面所列举的三个定义在这一点上完全无法帮助公众:“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耶稣基督本人不也粗暴地对待圣托马斯吗?后者要等亲眼目睹之后才肯相信,耶稣基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社会生活建立在信任和委托他人去核实的基础上。当我们在传播一条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时,我们也是假定它已经被证实是真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显然,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人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沃伦报告疑窦丛生。他们认为报告中的论断根本没有经过证实: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人的孤立行动。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最后,将谣言定义为正在流传而未经“证实”的消息,公众将更难以辨认谣言,尤其是谣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最为理想的证明,即直接的证明:“我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从爱丽舍宫驶出一辆救护车。”谣言总是通过朋友、同事或亲戚传到我们身边的,而且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还有什么比目击者更为可靠的呢?还要等什么更好的证明呢?这个目击者具有一个自发且无私的记者身份:他之所以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仅仅是出于和朋友们进行交流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愿望而已。
因此,所有以“未经证实”来作谣言的定义时,逻辑上总是说不通的。而且无法将其与众多其他通过口传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流传的消息区分开来。假如我们回到战争情报处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制止谣言呢?总不能禁止美国人民相互交流吧,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人们惶恐之极,更需要相互交谈,以求减轻焦虑之情。纳普提出的旨在制止谣言大量流传的五条“建议”颇为有趣。它们无意中揭示了为什么在任何时代,谣言总是使人尴尬的。它们是:
第一,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无保留地信任,使之勿需另求信息。
第二,必须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诸位领袖,并相信政府在尽最大努力解决战争和危机带来的问题。必须竭尽一切努力避免不信任与怀疑,这种不信任与怀疑会形成培植谣言的土壤。
第三,当某个事件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是尽快播发尽可能多的信息。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谣言满足了人们理解扑朔迷离的事件的需要。
第四,播发消息并不能保证信息被接受。因此最好能确保所有的人都接到这些消息。必须消除一切未知(一无所知)的空白点。比如,纳普就曾以英国军队的一项创举为例:组织“教育会议”,会上,士兵们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并且得到最清晰的回答。
第五,既然百无聊赖会渴望获悉哪怕最微小的传闻,以消除生活之单调,那么通过工作和业余生活的安排,使人们避免太过空闲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要求全民族共同努力,纳普的这些建议似乎是合法的,可以实行的。然而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时,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第一条建议反映了对非官方传播媒介的疑虑:倘若人们到别处获取信息,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有关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官方传播媒介播发的说法可能不相吻合。第二条规则是对领袖们的赞歌:公众必须对国家、城市、企业、工会、政党的领导人保持绝对的信任。第三条和第四条都是为了保证人民能接受官方的说法,排除一切信息的空白点。如果不知道官方的消息,这个空白点就会产生自己的事实。最后一条规则是建议妥善安排人民的时间:必须消灭空闲时间和无所事事。
因此,在谣言的定义中,强调谣言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属于人们对谣言的怀疑最为激烈的历史阶段。这类定义显然不能使人满意,因为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未经证实”标准带有主观性,它们无法区分一个通过口传媒介而获悉的谣言和一则从晨报中读到的消息。我们委托别人去核实,但我们却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所获信息已经证实。因为谣言的出现总是源于一个直接目击者的叙述,它和任何其他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一样,从表面上看已经得到了证实。
事实上,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来定义谣言,是意识形态上的定义,反映了反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纳普的规则在和平时期似乎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它们的功勋在于明确地指出了偏见的根源。谣言并不妨碍人,因为谣言是“虚假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把谣言放在心上。然而,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如泄密和政治内情的曝光。谣言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针对官方说法,别的说法也接踵而至:双方各有各的真实。集体议论
那么,是不是所有口传媒介的消息都是谣言呢?要是那样的话,则在社会上公布的所有新闻均可被冠以谣言的称号,甚至连向全市通报当天早晨总理在巡视市政府时发表的谈话也将无法幸免。因而,当我们想把这种传播定性为谣言时,我们却颇感迟疑。显然,如果某人询问一组人:“什么是谣言?”得到的答复决不会是官方消息或总理演说之类。因此,谣言的定义应该排除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合法地传播官方消息的现象。
最著名的对谣言的定义应归功于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他的充满了活力的定义是: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他认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举例说明:夜间,几十辆坦克穿过了一个突尼斯小镇。在这个新闻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人们就产生了疑问:发生了什么事?谣言便出现了,它是“一群人智慧的汇总,以求对事件找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参考书目137]。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希布塔尼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坦克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卡扎菲又重返突尼斯了?是不是因为物价上涨引起了暴乱?也许仅仅是一次演习?是不是布尔吉巴①死了?”在相互传播事件并加以评论时,这一群人逐步得到了一个或两个解释。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演变和添油加醋的评论。
我们可以将希布塔尼的论点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出来:
谣言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
这是一个乘法关系:假如重要性等于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比如,人们总以为在市场上买东西最易传播谣言:这是一个错误观念。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很少关心他们的牙膏或酸奶酪,大多数产品都很少同麻烦有牵涉。而且,这些产品并无何含糊不清之处,它们一目了然。
在消费领域需要大做广告并非偶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