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风骨
束星北:科学界的“陈寅恪”
谢:最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几年前。我喜欢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记得上面曾发表过一篇介绍束星北的文章,当时的感觉是,中国还有如此聪明的物理学家。作家出版社出了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想到前几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如果这两个传主好有一比的话,可以说束星北就是科学界的“陈寅恪”。
丁:很多年前,我也听王一方说过束星北,当时他在青岛出版社,我帮他组织过一套丛书。从他那里,知道束星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但是看了刘海军的书,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撼。以前还没有人把束星北和陈寅恪相比过,因为两人的专业不同,个人命运也不相同。但有一点不约而同:陈寅恪表示了如果让他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请允许不宗奉马列主义的时候,束星北也向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他们在当时都是有独立信念的人。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力图坚守专业的底线。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两个人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说是独立知识分子的缩影。
谢: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命运比束星北更惨。他在束星北被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郁郁而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丁:纵观束星北的命运,不能不思考一个事实,同行、同事和同学,在1949年时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看不出什么差异,但几十年后一比,人们多有叹息。
谢: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在美国的哲学家王浩回中国来,当时穆旦去看他,两人感慨万千。他们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但几十年后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而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穆旦,却当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临终前,才重现于文坛。
丁:陈寅恪当年也有大体类似的情况。据说那时傅斯年开过一个名教授的名单,但许多人没有听他的劝告,其中多数人的命运不好。像陈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国难得的奇才,可惜最后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他走了,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吴健雄是束星北的学生,她在美国也取得辉煌的成就。
谢:如果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连束星北这样纯粹的科学家,都要视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丁:在时代和个人之间,虽然我们不能说个人完全没有责任,但个人的命运最后是由时代决定的。个人是无力和国家对抗的。
谢: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如果在中心是不是会好一点?
丁:从个案观察,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因素,但还是时代的问题,中心也有许多悲剧。你可能注意到了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关系。他们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又是好朋友,但王的命运却顺利得多。当然与他后来从事国防方面的研究相关,加上他的个性平和,所以命运不同。
谢:我不了解王淦昌。但他能在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按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说明他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平和二字。可能和束星北相比,他不那么锋芒毕露。像束星北那样,在王竹溪被山东大学请来做学术报告时,跳上讲台,当面弄得他下不来台,个性也太强了。中国是一个讲面子的国家,束星北这种个性,是比较罕见的。
丁:天才人物都是富有个性的,难免被看成怪人。我们常常感慨中国的科学和学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人才,而是有人才不知道爱护。50年代,山东大学要送青年物理教师到前苏联留学,其实束星北的学术造诣在前苏联物理学界之上。李政道在“文革”中期回大陆,当时领导人说中国出现了人才断层。李政道说,他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大陆。
谢:中国文化中本来有敬重读书人的习惯。但经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丁: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保持平衡?而最后受伤害的又总是这些天才?
谢:不光是怎样对待天才的问题。那个时代,正直、坦荡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天才更是在劫难逃了。特例什么时候都有,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普遍命运不好确实是一个基本事实。
丁:这本书的写法也很有意思。全书有三个声部:一个声部是原始档案,一个声部是作者对知情人的口述采访,一个声部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三个声部互相穿插,构成一部深沉的历史交响乐。
谢:在近年的出版物中,此书无疑是少有的力作。作者为写这本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问。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十五年磨一剑。作者对传主活动的历史背景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这在浮躁的年代都很难得。
被遗忘的国士伍连德
丁:最近,我读了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感慨良多。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的科学家,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
谢: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我过去读过一本《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由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其中就有伍连德的自述。
丁:伍连德出生于南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回中国办学。1910年东三省鼠疫突发,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并迅速动员朝野力量,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日等外国势力,用四个月的时间,成功地阻止了鼠疫的流行。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谢:1910年东北鼠疫的防治,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了一篇论文,前两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丁:前几年,我们经历了非典,亲身体验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面对非典、艾滋病、禽流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中国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某种意义上说,在1910年就遇到过。只是伍连德积累的经验,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才想到他的可贵。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是二十多所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者,是禁毒的先驱者,是中国收回海港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
谢: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三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年底,山西晋北肺疫流行,也是伍连德负责处理的。晋北疫情过后,也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予曹树基。伍连德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之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也有记载,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丁:伍连德的功劳这么大,为什么在中国被遗忘?固然可以把理由归为他晚年居住于南洋,和大陆没有来往。但身居南洋的他,并没有被国际医学界遗忘。所以,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有特定的尺度。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的名字就家喻户晓,成为救死扶伤的象征。白求恩当然值得尊敬,他的故事应该传播,但救死扶伤的英雄不只是白求恩。还有伍连德这样的人。试想,如果能把传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于介绍伍连德,他能长期屏闭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吗?在医药卫生领域是这样,在科学、教育、经济、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都被长期遗忘。这使得我们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过于狭隘。
谢:王哲先生学医出身,有健全的历史感,文笔也很好,不知为什么以前没有读到他的著作?
丁:这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传记。但在此之前,他以京虎子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介绍汤飞凡的长篇传记,也很有分量。汤飞凡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在国际上被称为“衣原体之父”。但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却因不甘受辱而自杀。可惜此文至今只在网上传播,还没看到纸介出版物。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看到这篇文章,才产生和京虎子联系的愿望。
谢:我们的史学,我们的传媒,如果只知道围绕某些指挥棒打转,只会鹦鹉学舌,不知道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必然导致一代代的读者只能接受片面残缺的历史图景。今人不知道伍连德、汤飞凡不足为怪,后人不知道蒋彦永、高耀洁也不足为怪。
徐璋本的思想
谢: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从美国回来,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可能看过我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过清华的一个教授徐璋本,所以我想和你谈谈这个人。
丁:《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中提到过,比较简略。
谢:其实对这个教授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那年我在香港看到一些反右时的材料,其中有一个关于徐璋本的情况汇报,是新华社给高层的。我看了那个东西,感觉到徐璋本当年的许多想法,从民间思想史的意义上观察,不能忽视。
丁:黄肖路这次回来,我们也见了两面,但没有谈到徐璋本。
谢:黄说,当年徐璋本与他爸爸关系很好,两家走动很勤。徐是1954年从美国回来的。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大概住了20多年监狱,平反后,于1988年去世。
丁:历史研究的意义,有时候是与记忆相关的。如果没有历史研究,许多对历史有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就会被遗忘,所以对于那些早年贡献了自己思想的人,我们都不应当忘记。
谢:徐璋本有几个孩子,听说都有出息。不过一个人长年与家人分离,感情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再说在那样的时代里,因为父亲的关系,带给孩子的多是不愉快的回忆,可能家人也就不愿意提起了。
丁:越是这样,越需要研究历史的人来帮助回忆,不然历史就没有意义了。
谢:徐璋本当时在清华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他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右派,而是反革命,主要是他写过一些否定当时革命理论的文章。关于他的情况,当年《新清华》上有一些,如果要研究,可以去查一下。黄肖路告诉我,那时她很小,但记住了一个批判徐璋本的观点。说徐从美国回来以后,最不适应的是保密的事太多,什么都保密,什么都不敢公开,这怎么行呢?他就提了一些意见。
丁:长年在外的人,肯定适应不了当时的社会。我也看过你那篇文章中介绍他的情况。应该说,在1957年,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谢: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提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错误。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信奉“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某某学说为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会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性,鼓励消极自私心理。徐璋本认为,马克思的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
丁:他有没有比较系统的文章发表?
谢:1958年中科院学部办公室内部印过一本《右派文选》,里面收了徐璋本一篇长文《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非常系统,有两万多字。这几年中国思想界谈到的许多问题,他全谈到了。甚至国际问题,徐璋本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丁: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家,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学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看来中国需要研究的知识分子还很多,民间思想史研究还大有可为。
社会贤达的作用
丁:“九一八”纪念日,我去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借这个机会,我参观了纪念馆。其中有一幅关于1936年“七君子事件”的图片。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共产党当时得了分,国民党丢了分。七个人当中的邹韬奋病逝,李公朴遇害,其他几位在新政权中大多都做了高官,只有王造时受到冷遇。1957年,章乃器、王造时成了右派。但他们的命运,至今还常常被人提起。我就想,七君子当时的角色,是不是属于社会贤达呢?其中多数是持超党派立场的,应当算社会贤达。
谢:在民国时期,社会贤达站出来发表独立的声音,是常有的事。章乃器、王造时他们,也不只是敢于发出和国民党不同的意见。1941年,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拿中国领土做交易,他们也以致斯大林一封信的方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封信由王造时执笔,“老大哥”恨上了他,他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冷遇可能与此有关。
丁:社会贤达,就是政府以外的知名人士。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朝在政治、外交、司法、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民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承担上下之间的润滑作用,有时候,社会贤达的力量对化解冲突能起到特殊作用,国家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种社会力量。后来的社会结构中,不是没有构成这种群体的人员,而是国家的结构里不能容纳这种中间力量。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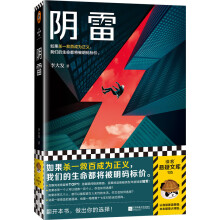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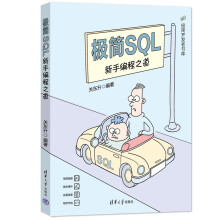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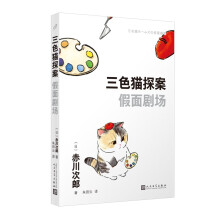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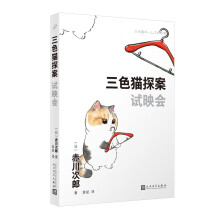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章诒和
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不仅因为直率、中肯,而且现实感和历史感兼备。两位学者以言语平实见长,还善于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在陈述和评判之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两位的观点与关切最容易引人分享和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
在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又变幻不定的社会“表象”之下,探寻某种“基准色”,委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
说昔日的教育,是为了冲现在的教育拍砖。拍到点上,砖砖都砸到七寸,这样的“砖家”多了,中国的教育也许有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