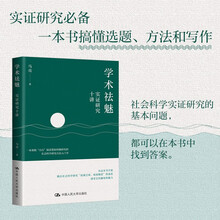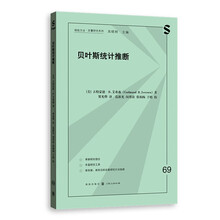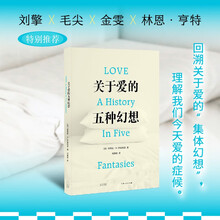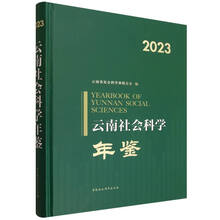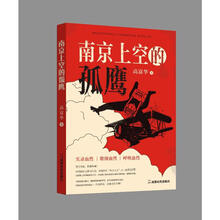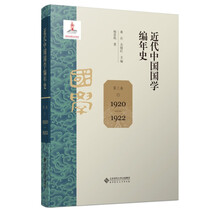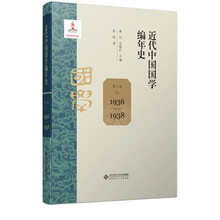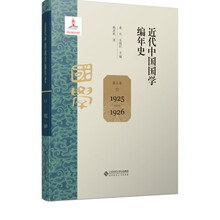四 关于“确证感”
前面已经说过,人类要实现自我确证,就必须有一个对象;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确证,就必须有一个中介。但是,对象也好,中介也好,都只能为人的确证提供条件,即只能提供人的确证的可能性。至于人是否在这个对象或这个中介那里得到了确证,却仍然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人的确证本身,也是需要确证的。
那么,人又怎样才能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呢?显然,只能通过一种心理形式。因为人的确证是对人的证明,不是对物的证明,因此不能借助诸如数学公式和测量标准等外在客观手段,用数学或物理学的方法来进行;而对象也好,中介也好,都只是“物证”和“他证”,人的确证却归根结底是一种“自证”,即对自我的确证。因此,它必须能为每个人自己所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作为人已经得到了证明,他自己却不知道,这就等于没有被证明。这样一来,人的确证,就只能诉诸人的内心体验,即只能通过一种内心体验来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事实上,正如人只有在感到自由时才自由,在感到幸福时才幸福,他也只有在感到自己被确证时才被确证。这就说明,人的确证,是要由确证感来证明的。
事实上,人的确证,也确实是由确证感来证明的。母亲疼爱婴儿,猎人炫耀猎物,小男孩因水面的圆圈而惊喜,艺术家因遇到了知音而激动,这些都是确证感。正是靠着它们,人确证了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而那些不能使人体验到确证感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的确,人最早是在劳动中,在自己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确证感的。当一个原始人捕获了一头猎物或打制了一件工具时,他会像一只猫逮住了老鼠一样感到兴奋。但是,猫的兴奋也仅仅只是兴奋而已,它不会因此而爱上那只老鼠。然而人却会爱上那猎物和工具,比方说到处拿给人看,向人炫耀,或是用它们殉葬。显然,在这里,猎物和工具已被看作了人自我确证的对象;人在劳动中体验到的也不仅仅是兴奋,而是确证感。
于是,人从此就获得了一种心理能力,即通过确证感的体验,在一个属人的对象上确证自己的属人本质。可见,确证感,是人确证劳动的心理形式,也是人确证自己得到了确证的心理形式,是“确证的确证”。它对于人来说,无疑极为重要。因此,它不可能是某种特殊的、罕见的东西,而只可能是极为普遍、寻常,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体验的。这种心理能力也不可能是个别的,而应该是人人都有的。我认为,这种“人皆有之”并“无时不在”的心理能力、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和心理体验,就是情感。
什么是情感?情感就是人在一个对象上体验到自我确证的心理过程。
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无非爱和恨。爱,显然是人的一种自我确证。我们爱祖国、爱家乡、爱父母、爱亲人、爱自己的劳动成果,都无非因为这些对象或者使我们成其为人,或者证明了我们是人。事实上,一切能够引起人们爱的情感的对象,都无不最能提供这种证明。如果这些对象不能提供这种证明,或不被看作是对自己的证明,那么,无论这些对象在理论上是多么地“应该”被爱,也仍不能被当作爱的对象。所以,尽管母爱常常被说成是人类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甚至被说成是人的一种“天性”,但在实际上,只有那些以生儿育女为女人天职、为女性自豪的人,才会真正有母爱,而那些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女人,其对子女的态度,却可能会“禽兽不如”。
爱是人的自我确证,恨则在表面上是人的不能自我确证,因为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情感。那么,人会恨谁呢?一般的说,人们不会仇恨自然,或其他非人的对象,因为它们即便不能证明我们是人,至少也不会证明我们不是人。我们最恨的,是那些不把我们当人、不能证明我们是人,或使我们不成其为人的人。正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人或会使我们不成其为人,所以,我们也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说他们“不是人”甚至“不是东西”。从理论上讲,仇人也是人。即便“不是人”,至少也是个什么“东西”。然而,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恨之人骨时,就会说他“真不是个东西”。因为对于人来说,即便一个“东西”,也是应该能够证明人之为人的(比如劳动工具就是)。现在,那家伙作为人,却居然不能证明人之为人,当然也就连“东西”都不是了。
然而,一个人如果连“东西”都不是,应该说也就无足可恨。比方说,我们不会也不能去恨一只猫或一条狗,一块石头或一根木头,因为它们原本只不过是“东西”。那么,一个连“东西”都不是的东西,又有什么可恨呢?就因为他原本“不是东西”,而是人。是人而不能确证人是人,这才特别可恨。然而,也恰恰正是在恨中,人同样实现了他的自我确证:一方面,恨是一种只有人才有的心理能力,我恨了,说明我是人;另方面,如果我不是人,又何以能够判定对方“不是人”甚至“不是东西”?因此,恨也是人的自我确证。它曲折地又双重地确证着我们是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