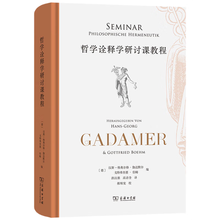第一章 人文研究
我想从认知革命说起,这场革命在经历了客观主义的寒冬之后。试图将“心灵”带回人类科学领域。但是,我的学说不是简单地描述这一勇往直前的历程。因为至少在我们看来,这场革命现在已转变为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当初催生它们的推动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认知科学已经被技术化了,甚至于被削弱了当初的推动力。这并不是说它失败了:恰恰相反,因为认知科学注定是学术交易所中成长最快的股票之一,它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这种胜利是在付出高昂的技术成本后获得的。有些批评人士——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新的认知科学作为这场革命的产物,已经取得了技术上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是让心灵这个概念失去人性化。而它一直追求的就是重新确立心灵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凶此,它使心理学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人类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开来。
我将进一步简短地阐述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为您列出本章以及后面几章的计划。当我们回顾完那场认知革命后,接着会对即将再度兴起的革命进行初步的探索。这场革命更倾向于解释与“意义构成”相关的认知,它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扩展进入人类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心理学的领域中,时下,差不多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我甚至怀疑如此强劲的发展可能会重拾当初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势头。我将在后面几章里对某些研究进行初步但具体的阐述,这些研究以心理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中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为目标,而且具有当初认知革命的那股发展势头。
现在,先让我来阐述我和我的朋友们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的那场革命的想法吧。我们认为,它试图竭尽全力将意义确定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不是刺激和反应,不是明显可能观察到的行为,也不是动物本能及其转变,而是意义。它不是一场反对行为主义的革命,其目标也不是通过往行为主义中加入一点心灵主义使之成为更好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曾经那样做过,但收效甚微。那场革命要比这深刻得多,它的目标是发现并正式地描述人类与周围世界交流时所产生的意义,进而提出与意义生成过程相关的假设。它关注人类在描述和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自身时所进行的符号行为,其目标在于加速推动心理学与其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辅助性姊妹学科携手发展。实际上,表面上认知科学日益计算机化,但以上所说才是真正的事实——起初是缓慢推进,现在其动能不断增强。所以,如今人们发现文化心理学、认知和解释人类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中心一派繁荣。总之,自从康德关于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出现之后,这一领域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进取性。它很可能成为时代性标志,代表人物是1989-1990年在耶路撒冷一哈佛联合讲座的主讲者们,他们有着各自的方式和传统——格尔茨(Geertz)教授在人类学领域独树一帜,而我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
正如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要求心理学与人类学和语言学、哲学和历史,甚至于法律学形成合力。所以,在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 at Harvard)成立的初期,组成人员中有一位哲学家奎恩(W.V.Quine),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和一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这毫不奇怪,也绝非偶然。或者说,中心内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中还有诸如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新构造主义的倡导者——在数量上与心理学家不相伯仲。至于法律学方面的代表,我必须说明,该中心的几位著名法律学专家只是偶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们当中的鲍尔·弗莱德(Paul Freund)承认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来到中心,他所感兴趣的是,规则(比如语法规则,但不包括科学公式)如何影响人类的行动,以及法学究竟需要研究什么。
我想现在应该向您说明,我们不是要站出来“改造”行为主义,而是要替换它。正如我的同事在随后几年里说的那样,“我们将我们的新信条钉在门上,而后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是非常地顺利,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是白白地为我们能否取得成功担心了那么久。”
如果写一篇关于上个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学术史的论文。追述认知革命的原动力以及它分裂、技术化的过程,肯定会引人入胜。完整的故事最好交给那些睿智的历史学家去写。现在,我们需要弄清的是沿途的标志牌,它们已足以为我们指明即将前往的知识领域内的情况了。比如,很早之前,研究重心就从“意义”转向“信息”,从意义的构成转向信息的处理,这些都是影响深刻的变化。这一转折中的关键要素是计算作为主要的隐喻方法而被引入,以及可量化计算成为好的理论模型的基本标准。信息与意义的关系不大,从计算的角度来说,信息由系统中未进行编码的信息要点组成,而意义要经过归纳才能成为信息要点,它既不是计算的结果,跟随机分配式的计算存储也没有关系。
信息处理是指根据中央控制单元的指令,在存储地址上记录或获取信息要点,或将其暂时存在缓冲存储器上,然后按照指定的方式操作:列表、命令、组合、对比未编码的信息。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系统对其存储的是莎士比亚诗歌中的文字还是随机数据表中的数字均一无所知。根据典型的信息理论,如果一个信息要点减少了可能的选择性就具有情报价值。这就暗含着一个锁定某种选择的代码,可能性序列和它们包含的例证要按照系统中的“语法规则”——可能出现的变化情况——进行处理。到目前为止,这一分配系统中的信息仅能处理字典层面上的意义:根据经过编码的地址评估存储的词汇信息。还有其他“类似意义”的操作,如改变一系列条目的序列,以便按照标准测定其效果,就像在拼字游戏或字谜游戏中那样。但信息处理不能应对既定范围之外的任何东西,对于那些能够随机进入特定关系的条目也无能为力,这种特定关系被基本操作程序严格控制。这样的系统不能处理模糊的、存在分歧的、隐喻的或内在的联系,如果非要它这么做,就好比让一只猴子进入了大英博物馆。它只能机械刻板地按运算法则来解决问题,或冒险去试探不确定性。信息处理需要提前规划并拥有准确的规则。它排除了类似不严谨的问题:如“穆斯林正统派人士头脑中的世界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或“自我概念在希腊荷马时代和在后工业时代有什么不同?”它倾向于解释类似这样的问题:“按照怎样的最优战略为操作者提供控制信息,才能确保车辆在预定轨道上行进?”我们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意义及其产生过程,它们与传统上所谓的“信息处理”距离之远让人惊讶。
后工业时代的信息革命早已遍及全世界,因此出现这样的论断毫不奇怪。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通常都是很敏感的,它们对其所处社会的需要经常是过于敏感。理论心理学总是本能地按照新的社会需要去重新定义人及其心灵的涵义,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者的兴趣相应地从心灵和意义领域转向计算机和信息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计算机和计算机理论基本上已成为信息处理的代名词。先前在一定领域内确定下来的健全的意义分类足以为操作代码提供一个基础,因而装有适当程序的计算机就可以进行一些最低限度的操作进而完成信息处理,从此计算机应用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不久,计算成为心灵的范式,并取代了意义的概念,新的概念——“可计算性”出现了。认知过程与那些可在计算装置中运行的程序等同起来,比如说,一个人在“理解”上的成功,如记忆或概念获得,实际上成为了人们用计算机程序来模仿人类形成概念或记忆的能力。这一思考方法得到有开创性深刻见解的图灵(Turing)的大力佐证,他认为:任何计算机程序,无论它有多么复杂,都是“仿照”极为简单的普适图灵机(Universal Turing Machine)的功能,依靠一组原始的简单操作来完成工作。如果有人习惯于将那些复杂的程序看成是“模拟的心灵”——借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那么他再往前迈出关键的一小步,就会完全相信“真实心灵”及其形成过程同模拟的心灵及其形成过程是类似的,均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来“解释”。
新的简化论为正在生成的新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自由论程序,它非常之宽泛。实际上,哪怕是早期的刺激一反应学习理论者和研究记忆的联想论学者,只要他们将自己的旧概念用信息处理的术语包装一下,就都能回到认知革命的阵营,这与“精神”过程和意义毫不相干。取代刺激和反应的是输入和输出,情感污点被转化成一种控制元素,而控制元素将操作结果的信息反馈给系统,进而使对情感污点的清洗得到强化。因此,只要有可用于计算的程序,“心灵”的概念就可以产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