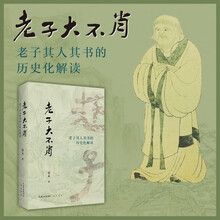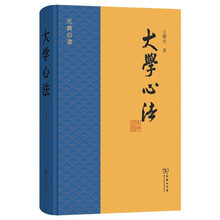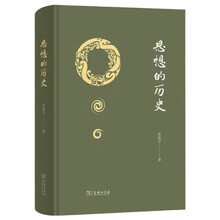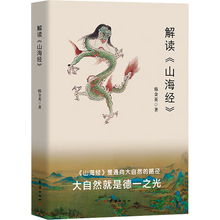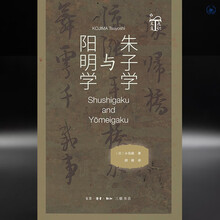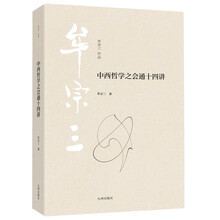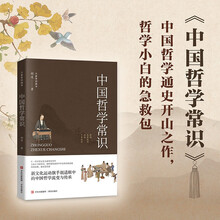历史所求的是过去,由过去即能知现在。然而过去、现在、未来,莽莽迁流而不息,本无界域之可分。此即所谓进化。欲知此进化的定则,必明事物的因果。史学与史料之别,即在史学所求者,在事物的因果,在进化之则。不仅史事流转不息,历史本身亦“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而改作不仅是纠谬补阙而已。时代变迁,人对历史的着眼点亦随之而不同;所见既异,所取材料不得不异。①可见诚之先生治史,是以著新史为鹄的,与新旧考证派祈向不同。
在先生看来,古人作史的宗旨,有三点与今人不同,即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军事。“政治军事,古多合而为一。而握有此权者,苟遭际时会,恒易有所成就,而为世人目为英雄也。此最大之弊。”政治对社会的影响,愈至近世而愈轻(政治转移社会之力,近代实远不如机械发明)。而军事的胜败,“初不在胜败之时”。②须知凡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先生以韩信与戚继光将兵事为例。韩信驱市人,背水列阵,竟打胜仗。戚继光重视训练,所部纪律严明,亦所向有功。二事恰相反。重视战术的人,以为韩之将才胜于戚;重视训练的人,则说韩信成功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战国时代,本是举国皆兵。韩信生于汉初,一般人民承战国之风,都有战斗技能,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人自为战。戚继光的时代,人民全不知兵。“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足见欲知史事真相,必须明了其环境。
若不知环境,对任何事情,乃至任何时代,都不能明白。所以现代史家最重要的事,是“再造既往”,亦即“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可分“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两类。就特殊事实而言,和普通的见解相反,往往隔相当长时期,然后真相大白。因为事情有其内幕,当时秘而不宣;而且当时人论事,难免因利害和感情关系,见解不能平允,故真相历久乃明。至于一般状况,则与之相反。以上海的情形而论,“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