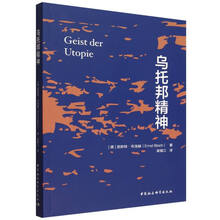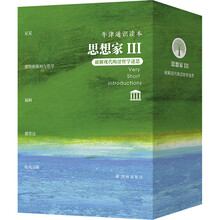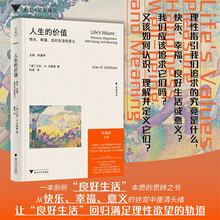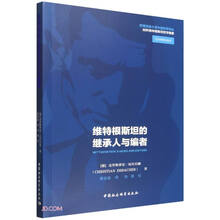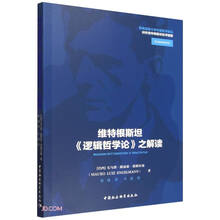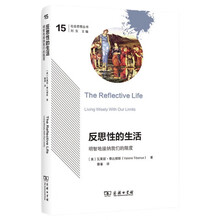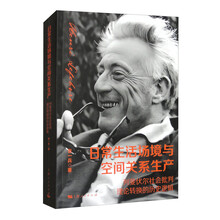第一讲 遭遇人世间的阴暗面
颜回见仲尼,请行。日:“奚之?”日:“将之卫。”日:“奚为焉?”日:“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石工,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日菑人。苔人者,人必反菖之。若殆为人苔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庄子笔下的人间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可谓是礼崩乐坏,各诸侯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象经常发生,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孔夫子对于这样的局面,完全无可奈何。道家学说,特别是庄子,对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得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从庄子的角度看来,当时整个社会极为险恶,整个人心也极为险恶。怎样在这种险恶的社会、人心环境之中,以不变应万变,使自己能够养生、全身、保命?这些问题就是《庄子·人间世》这一篇中很重要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从佛教的理论来看也是如此。佛教把这个人类社会称为“五浊恶世”,这与庄子在《人间世》中表达的思想,是非常契合的。人世间有它阴暗的一面,有它险恶的一面,但究竟是怎样阴、怎样险呢?通过《人间世》中颜渊与孔夫子的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二。
另外,从本篇颜渊与孔夫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暴君,处浊世,与人交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文章通过层层推进,层层辨析,最后引出了“心斋”的学说。所以《人间世》的这一段,在整个《庄子》的三十三篇里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庄子》三十三篇里,只有这一篇是大量地、深入地介绍了人世间的阴暗面。
好,下面我们看正文。
文章一开篇,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即是颜回去见孔子,向他辞行。孔夫子就问他,你要到哪里去呢?颜回说,我要到卫国去。孔夫子又问他,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啊?颜回就说出了自己的抱负:愿意以自己平生所学,去救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
颜回跟自己的老师说:“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日:‘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我们来看看卫国的国君是什么样的人。“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这是一个年轻气盛,办事专断的国君。其实,不光是国君,就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都容易犯这种错误。特别是既年轻又有权的人,往往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不明白怎样应对身边的环境,自然就会“其年壮,其行独”。
轻用其国的后果
从历史的经验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是这样干的。修长城,动用一两百万人;南开南越,动用五十万人;修骊山陵,又动用七十万人。后来还修了阿房宫。那个时候,搞得全国再也没有壮丁在田里干活了,老百姓只要稍微有点过失,就充军发配!葬送了秦朝的汉高祖刘邦,当年也好几次带着服劳役的人到咸阳去,最后一次由于不能按期到达,要受惩罚了,才起来造反。再看楚霸王的战将黥布(后来称为英布),脸上刺了字,是犯人,也曾参加骊山陵的修建,只不过他命大,逃出来了。秦始皇这些“其行独”、“轻用其国”的行为,弄得民怨沸腾,他去世的第二年,全国就爆发了推翻秦王朝的大起义。
隋炀帝也是轻用其国的典型。他修大运河,还连续几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开运河以后多次巡行江南,铺张浪费,不问国事,最后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再往后,被金人掳去的宋徽宗,他要地方上进贡花石纲,也是这个样子。从浙江弄到首都开封的石头,小则几吨,大则几十吨,从陆路、水路一直运到开封。石头还要这样布置、那样打扮,弄得花里胡哨的。人民不堪其扰,沿途的老百姓简直活不下去!
“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这是肯定的,因为你不爱惜民众,那么“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人命就像草芥一样不值钱,死者如山。户籍史料显示,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到刘邦统一天下时,全中国就只有五六百万人了。算算看,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死了多少人?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是“十余二三”。
到东汉末年,官方的全中国人口数字是六千多万,为历朝历代(清朝以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时期。(就算唐朝“开元盛世”的时候,全国也只有五千多万人。)然而,经过了三国的纷乱,这么多人口到了“三国归晋”的时候,全国就只有五百来万人了!在我们四川,刘备的这块地方,只有八十多万人了,其中部队就有十多万人,且不说还有那么多的行政官僚。老百姓基本上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士兵,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孺,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国家根本拖不动!东吴比蜀国好一点,那时候也不过一百多万人;曹魏实力最强,也不过三四百万人。到了“三国归晋”的时候,全国也就五六百万人!相比之下,人口竟然骤减了十分之九!
隋文帝统一天下后,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隋朝其实已经相当富裕了,文治武功并不比唐太宗的时候差。但给隋炀帝那么一折腾,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统计户籍的时候,也只有几百万人,不到一千万。由此可见,只要遇上了劳役、瘟疫、战乱这样的事情,就很可怕了!
我们举了这么多远的和近的例子,应该有所体会了。所以到现在,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害怕国家混乱!一进入战乱、暴乱这么一种状况,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真的就危险了!十三四亿人到时候拿着这个烂摊子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像古人说的那样,“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先自度而后度众生
颜渊跟着孔夫子学圣贤之道,看到卫国的国君胡作非为,“民其无如矣”,老百姓都没有办法,没有可归之处了,所以就对孔夫子说:“回尝闻之夫子日:‘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你老人家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一个国家如果治理得很好,你就没有必要再待在那儿了,你应该到乱国去,到那些没把国家治理好的地方去效力!高明的医生,面前永远是病人多多。我愿意根据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到卫国去,帮助它解决政治问题。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把卫国的这些麻烦给解决了。
颜回的这个发心肯定是很好的,儒家的观念里,一个有理想的人,就是要去治国平天下嘛。然而,孔夫子这里却反对他去。为什么反对他去呢?按理说,颜回既然是按照他的教诲来办的,他不应该反对呀!我们再来看孔夫子的回答。
“嘻!若殆往而刑耳!”就你啊?嘿嘿,你要是到卫国去,谨防挨上一刀!不但帮不了卫国的忙,反而搭上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注意了!这个是一个大原则。孔夫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单列出来看。“道不欲杂”,在道家学说里面,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宗旨,就是抱元守一。道术忌杂,我们学、我们修、我们为人处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应该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不可能此时你在北京,同时你又在上海。所以道术忌杂是我们用心.做事的一个根本原则。
有的人是艺多人胆大。艺多了,你未必能精。你要专精,就必须要集中精力和时问投入。很多人像猴子掰玉米,今天干这样,明天干那样,结果一件事都料理不好。这就犯了道术太杂的毛病。所以庄子的这一句,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为人做事,一定要抱元守一,不要去多想多为。
“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这个道理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你一杂了就多,多了当然会扰,干扰你的心智,干扰你的判断。当你事情多了以后,你东边也在救火,西边也在救火,东边去踩,西边去压。如果超出你能力的范围,超出你的可控距离了,那么你心里面自然就会担忧、发愁。“陇而不救”,当你从事上的麻烦变成心里的麻烦以后,谁又来救你呢?事情没干好,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料理好。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里,孔夫子开始谈“至人”,谈在道上有所得的人是怎样来处理这些事。至人是“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先要以道成就自己,让自己得道解脱,然后再去成就他人,按佛家来说,就是先自度而后度众生。
这又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就像带兵打仗一样,总是先要保存自己,然后再求消灭敌人。不先保存自己,自己牺牲了,就谈不上消灭敌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原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考虑到的。在日常的修为当中,一定要先以道来成就自己,有了这个本钱,你才能够“存诸人”,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如果自己还没有本事,没有本钱,在道上没有什么心得体会,那么哪有资格到“暴人之所”,去伺候这个暴君呢?用成都的丑话来说,就是自己屁股流鲜血,却给他人医痔疮。这简直就是笑话!
老庄哲学的根本原则
下面孔夫子继续教导这位心爱的弟子:“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孔夫子问颜回,你知不知道“道德荡、智虑出”是因何而起的呢?“德之所荡”,一个有德的人,他内在的魅力自然会释放出来。不仅仅是内德会释放于外,而且是“知之所为出”,智慧同样也会表现出来。但是,道德是怎么释放出来的?智慧又是怎么样释放出来的?我们道德、智慧的源泉到底在哪里?“德之所荡”,“知之所为出”,是我们修为过程中要认真留意的话啊!
孔子谈到这里,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话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德行与智慧的麻烦来。“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我们看到这几句话,大家都千万要留心!“德荡乎名”,你的德行一出来就有了名气,有了名气,你这个德,也就有点麻烦了。
中国佛教发展到南北朝萧梁时,有一个僧人慧皎写了部《高僧传》。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僧人写了个《名僧传》。但慧皎不用“名僧”这两个字,为什么呢?他说一个出家人,本来就是要合去名利的。我们修行,要脱离生死苦海,要合弃名利,怎能拘泥于名呢?真正有修行的人,应该是高僧,不应该称之为名僧。所以,慧皎就写了中国的第一部《高僧传》。那么他的这个本意,也还是出自《庄子》的“德荡乎名”。如果大家都成了名僧,大家的名气都大了,但恰恰名人未必就是高人。
你看现在庙头,这样职位,那样职位,今天坐飞机,明天当个CEO,煞有介事。前几天,我还和朋友谈到了那个“旅行大师”,把某某某这样一个著名寺庙当企业来运作,经常坐飞机去美国、去欧洲,带一批武僧到处表演。这些武僧,能武打,但佛法修行的水平又如何呢?
那天,我这儿来了一个河北沧州的,也参加过河北的禅修夏令营。这位朋友三十多岁,学武功,也学道术,也还很有成就的样子,能水上漂。据他说到东湖去的话,他可以在水面上从东岸跑到西岸,不会沉下去。另外,他说他的龟息术也小有所成,能够五花大绑地在坑里活埋五六个小时,没事儿!而且有脱逃术,同样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戴上,他可以在十秒之内脱逃。但收徒弟的费用就不低了,一万元一人,学一年,保证你能学会其中的一两样技能。他有这样的本事,都还想到成都来访高人。我给他讲了几位“高人”,他听了后说,算了,不学了。
当然我说的那些人,用的是术,不是道上的东西。我们再来看,德和智,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得的。德和智的修养,当然就是道上的东西了。但道上的东西,它又有所忌讳!德,因名而消失;智,因争而愈出!所以说“名也者,相轧也”。有了名之后,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比如在名次、排位上相争等等。有些人什么事都要争第一,千千万万的人,你要踏下去多少?踩下去那么多人,不累死你啊?
“知也者,争之器也。”我们的智慧,很多人也是用在对矛盾的驾驭上,用在争斗上。而且通过争斗,积累经验教训,这方面的智慧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这就叫智因争而愈出。如果智和德牵扯上名、利以后,这个德和智也就不善了,就是恶了。所以,“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我们看《老子》里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庄子》里,比老子的话更进一层了,把“名”和“智”也看成了凶器!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原本是很不错的,然而一旦有了名,出了名,就糟糕了。有些本来很憨厚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结果一变聪明之后,也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开启智慧了,掌握了世间的争斗之智、谋略之智,用于互相砍杀,别人对他就敬而远之了。所以说名和智,的确是凶器啊!
“非所以尽行也”,这些都不是究竟之道。我们知道在老庄的学说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弃圣绝智,这里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弃圣,就是要把孔夫子讲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等等抛弃不用;绝智,智慧也不能用,因为用智就有机心,有机心就与大道不合。大道是没有机心的,是自然的,而我们人心之动,往往是违反自然的,违反大道的。所以老庄学说的弃圣绝智的原则,在《庄子》中表现得非常之坚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