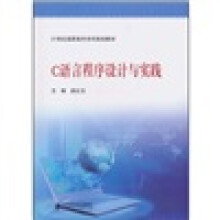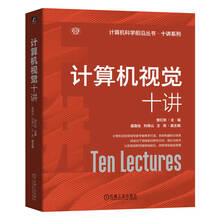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与上述路、程二位先生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运用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同样是深入的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简单的采写记录。但作为受到过民族学与史学两个学科训练的学者,马先生的研究比前者更具民族史的特色,他的口述史作业方法,也明显更接近于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中国大陆,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长足发展,且始终与民族学紧密结合。具体地说,它既是传统史学吸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结果,也是民族学家为“本土化”进行努力的一个方向。马长寿先生这部书,正是老一辈学者中将二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做得最出色的典范之一。该书从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来看,仍然是上乘之作,且与今天的历史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民族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两大史学发展趋势暗合。在中国口述史的学术史中,马先生和他的作品,无疑具有开拓地位。
口述史与民族学的田野作业有同有不同,正如口述史学与如今方兴未艾的历史人类学也有同有异一样,二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的学科规范,但相互间的借鉴与互补导致二者间的密不可分。有些学者也采取既做口述,又对被访者身处的环境进行参与观察的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只不过有些人类学家不肯承认这属于口述史范畴而已。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专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始大量参与到口述史的工作中来。不过,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沿着一条单一的路径,即先有部分学者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介绍进来,并指导国内学者从事实践的方式而展开。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大陆为数颇多从事口述史学实践的学者和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都是由这些学者直接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并应用于国内实践的产物,更有一些,则是受到台湾学界口述史的影响,因而出现一部分人致力于介绍和探讨理论、另一部分人一头扎进实地访谈,二者几乎互不相干的局面。不过,这倒反而使口述史的发展呈现一种“多源多流”的多元化特征,是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我国学界显示出蓬勃生机的重要因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