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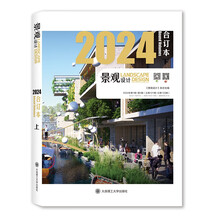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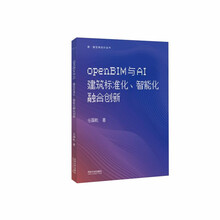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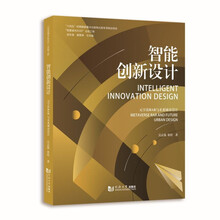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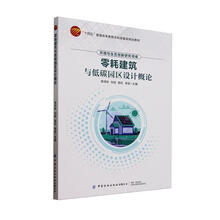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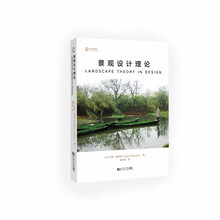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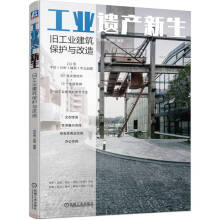
我想强调的是我的方法有些不同之处。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创造过程本身,即模糊性和隐喻性思维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似乎存在于我们的本质核心之中。简单地说,我认为当今神经科学向设计者所提供的是我们已有的极其精密的智商和情感草图。我这么说是不带任何惴惴不安之情的,即使这还意味着该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简易的答案。而且事实上,该研究很快被其自身的进度所超越。我们今天如果第一次将工作中的大脑意象置于其所有的复杂性中,那么我们距离构筑该过程中最后的基因和后生性遗传模型还要有好几年时间。为此,这个新拓展的研究领域对于年轻设计者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在神经科学这项知识的不断发展中,年轻的设计者们必将大展宏图。
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理论有实际的生物学基础吗?建筑师拥有很特别的大脑吗?当今的神经科学为建筑学提供了设计思路的新基础吗?
这几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由这个极其详细的研究提出的。该研究从两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即建筑师和设计师是如何看待现象世界的。在《建筑师的大脑》上篇,茅尔格里夫简要介绍了过去500年里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思潮,这些思潮是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方面的认知表现形式。在下篇,特别是由于当代神经科学在过去十几年里有所发展,因此作者从对当代神经科学的非凡洞察这一视角,重新定位了上述问题。这本书呈现了一些不朽的建筑思想在神经科学方面令人惊讶的确证,以及从建筑经验的多感知本质到模糊性和隐喻性相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必然关系。作者切实地论证了建筑——除了它对于人类智慧的刻意表现——根本上是根植于以生物价值为大前提的感情和感性经验,这并非是因为理查德?诺伊特拉的SurvivalthroughDesign(《生存设计》,1954)在建筑理论领域提出的具有启发性的议题。
计算机和建筑
在这里我有意使用这个可能引起争议的以及不祥预感的题目,是因为我想考虑一下计算机及其在建筑中的应用。几乎像所有人一样,包括前面提到的大部分批评家,我也特别感激数字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好处。电子连接、纳米技术、无线技术、全球化、最新搜索的即时共享——所有这一切都把我们领向举世无双的智力成就,并且极大地推动几乎所有领域知识的巨大进步。今天的世界与几十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了,并且总体上来说好于以前的世界。
计算机对于建筑师是大有裨益的也同样地得到了证实:计算机不仅把建筑师从以前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去做以及每一笔都要亲自动手去画的枯燥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得建筑师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下一代建筑信息模型BIM系统的出现,以及一体化大楼(包括建筑师、工程师、业主以及建筑者的无缝团队)交付承诺的出现,将理所当然地巩固这种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的转变。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数字时代中这些更加有效的工具将同样提高全球建筑质量标准,就像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经常看到的那些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同时在从事涉及到两三个大洲的特定工程项目那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计算机也是一种设计和建模工具,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它和任何一种别的设计工具一样看待。无论从肯定的方面还是否定的方面来说,计算机在创造性的意义上来说带给设计过程的全新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也许意识不到建筑的计算机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过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教育和设计实践完全集中在计算机上的学生来说——你们也应该知道你们基本上是第一代——在你们之前还没有建筑师是以这样的方式培训而成的。
作为一种用来准备建构文件的工具,计算机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几家精挑细选的公司里。但是它的广泛使用,特别是超越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改进,真正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弗兰克·盖里的设计室是使用计算机进行这方面实验的先行者之一。1989年这个设计室在考虑怎样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一个鱼雕塑设计画稿,与此同时,设计师们决定修正与航天设计相关的软件。盖里本人从来没有从事过与此相关的工作,作为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设计师,他更喜欢用草图、硬纸板以及埃尔摩胶水。然而,修正后的软件使他能够自由地思考诸如瓦尔特·迪斯尼音乐厅(始于1989年)以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始于1991年)这样的设计。毫无疑问这两个设计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一些其他的新软件把设计塑造成不同的维度以及细节复杂的表面,从而开辟了设计勘探的新领域。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建筑师都在探索非线性、分形、复杂性理论以及场论相关的设计策略。这个行业本身,至少从标志性层面上,从此由于以下的设计而巩固其成果:伊东丰雄设计的仙台媒体中心(1995-2001)、联合工作室设计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2001-2006),以及由德国人奥雷·舍人和荷兰人库哈斯带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设计于2002年)。所有这些形式上的创新都是由于新一代计算机的应用在最近短短几年时间里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的。
建筑学的计算机化也有许多自身的强烈拥护者,其中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也许当属威廉·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在他受星际航行灵感激发的《伊托邦(e-topia):城市生活——但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内容》(1999)一书中,他提出了怎样使得计算机能够变革城市生活的案例。在“低利润和绿色”的理念中包含了如下特性:比如说非物质化(减少物理结构的需求),非运动化(通过远程通讯降低燃料消耗),大量用户化(非标准化设计)。仅仅为了阐明最后一点,米切尔认为在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里展示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新型空间和材料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东西”引起人们“一种更加微妙的,更加复杂的理性”——任何人,除了一些“顽固不化的密斯式建筑的爱好者”。17最近在他的著作《Me++》中,米切尔为了表明他关于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本体主义的状态已经演变成机器化生物的状态之一这一信念,发起了一个更广泛的运动:
因此我不是维特鲁威斯人,被封闭在一个单一的完美的圈子里,以我个人角度坐标观看着外面的世界,同时,提供了测量世界万物的尺度。我也不像建筑现象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给自足的、生物学意义上所体现出来的主体,遇到我的周围环境,并把我的周围环境客观化,然后接受它。我在一个相互递归的过程中构建,同时我也被构建,这一过程不断地攻击我流动的透水边界和我无尽的错综交叉的网络。我是一个空间上无限延伸的机器生物。18
毫无疑问,米切尔是反对上文中德雷福斯的评论的。德雷福斯论述的目的在于评论创造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模型的各种努力。后者的这一目的最先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与兰德公司和卡耐基梅隆大学有关联的一批科学家发起了一个项目,意在创建一个能够与人的思维相匹敌的计算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想法如雨后春笋般在几十个博士班和政府设立的科研实验室里发展起来,那些研究项目到今天为止经常以失败告终。计算机及其软件却证明在解决复杂的量化问题方面有超凡的能力——任何量化问题,从飞行器的设计和天气预报到非线性分析——但是计算机在模仿人类的联想思维能力方面,被证明在最根本的水平上是完全不够的。
早期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努力之所以普遍失败原因非常简单。人类大脑的神经回路不是以正式规则的二进制体系发挥作用的,类似于加二加二;因此找不到比电脑摹拟人脑更错误的事情了。大脑在它的回路布线过程中是非线性的(非因果关系的),它潜在的传导途径是有冗余的,在它的体系组织中的复杂性远远高于现在人们所能想象的任何软件的算法规则系统。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已经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磨练,其中包括各种补充物质的层层覆盖或生物提炼加工,经历了神经效率的几何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导致达西·汤普森(DarcyThompson)露出惊讶的神情。比起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神经学家越来越惊叹人类大脑联想能力的复杂程度。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言,“如果大脑简单到我们可以搞明白它,那么就是我们太简单了——竟能够搞明白大脑”。19
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软件应用现在已经成为设计专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掌握软件应用应该成为建筑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不是对于学习设计的学生所进行的培训仅仅局限于通过使用计算机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建筑课程的方向恰恰相反。现在很有可能的是,在很多学校里进入设计领域的研究生,他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其他专业——这些学生除了受过计算机的设计培训外没有受过其他方面的设计培训。与此同时,非专业课的数目,比如说可能提供的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这么多年来却越来越少。因此,我关注的焦点在下面三个方面:
计算机作为设计的首要工具,往往在展示技巧上具有拉平效应,而在设计上别具一格,具有原创性。
计算机往往非物质化设计思想,从而导致与人类能够感知到的经验世界相去甚远的抽象性。
计算机设计往往并未充分利用人类大脑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我认为年长一些的建筑设计师,由于受过传统设计方法的培训,具有相关的经验,因此能够克服这些问题。而对于年轻一些的建筑设计师来说,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培训,不大可能克服上述问题。
......
简介
上篇 形形色色的大脑
第1章 人文型大脑 阿尔伯蒂、维特鲁威斯和列奥纳多
第2章 启蒙型大脑 佩罗、劳吉埃和勒罗伊
第3章 感知型大脑 柏克、普赖斯和奈特
第4章 先验型大脑 康德和叔本华
第5章 活跃型大脑 申克尔、波提奇尔和森佩尔
第6章 移情型大脑 费舍尔、沃尔夫林和柯勒
第7章 格式塔型大脑 感知领域的动态变化
第8章 神经型大脑 哈耶克、赫博和诺伊特拉
第9章 现象型大脑 梅洛-庞蒂、拉斯穆森和帕拉斯玛
下篇 神经科学与建筑学
第10章 解剖学 大脑结构
第11章 模糊性 视觉结构
第12章 隐喻性 体现结构
第13章 触觉 感觉结构
尾声 建筑师的大脑
尾注
参考文献
索引
这本书引人入胜地解释了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如何扩展我们对于建筑的理解,理解从阿尔伯蒂认为建筑是“身体构造”的理念到茅尔格里夫挑战计算机对建筑学的支配作用。
——大卫·沃特金,剑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