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玛·邦克的文章,主要结合1999年香港大学有关中国古代饰物的展览所作,对辽代琥珀作了专门探讨。作者认为琥珀对于契丹人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清人虽有使用,但其重要性根本不能与辽时相提并论。文章结合出土品以及传世品,对辽代佩饰的一些题材、设计、使用以及所体现的宗教含义,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亦提及琥珀对于契丹族的象征意义,以及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但未及详论。对于辽代琥珀来自波罗的海一说,认为应该做更多的标本检测,才可以下结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第一篇有关中国琥珀艺术,特别是辽代琥珀艺术的专题文章。它第一次凸显了辽代琥珀艺术的独特魅力,琥珀对契丹人而言可能存在的深刻内涵,以及据此可以引发的中西交通方面的深层探讨,可谓中国琥珀艺术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二 中国 中国有关琥珀的第一篇文章,是陈夏生1990年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上的《溯古话今谈宝石:琥珀》。这是有关宝石的系列文章之一。文章内容涉及有关琥珀的方方面面,如琥珀的成分、特性、名称的由来、各产区琥珀的特点、中国古籍记载中的琥珀、琥珀的辨伪等,涵盖许多常识性的问题。
文章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不少琥珀制品,如鼻烟壶、盒子、罐、手串、手镯、陈设性的琥珀山子等,展示了清代琥珀艺术的风采。这也是迄今为止首次馆藏琥珀制品的展示。文章未涉及对这些藏品的探讨。
苏芳淑在其2000年发表的《契丹玉和琥珀雕饰初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琥珀艺术在辽代艺术研究中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文章通过辽代玉饰、琥珀饰的材料、工艺、用途、题材和表现风格的对比,认为“契丹人用玉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味道,辽玉器的工艺、器形、题材和花纹都和唐宋玉器分别不大,因而或可将辽玉视为契丹人汉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相对来看,他们[契丹人]的琥珀饰件具备丰富的游牧民族特色,无论工艺、器形、用途和花纹— —特别是其重叠繁密堆砌的构思——都有它的别出的风格,所以辽代的琥珀饰物应当为契丹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因此,若要深入认识契丹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我们或应在他们的琥珀中寻找”。文章作为立论根据所分析的小型佩饰和饰物、各式盒形或瓶形佩、璎珞组佩类饰件,都是典型的辽代琥珀类型。所以,文章的主旨虽然是“希望通过辽代文化玉饰和琥珀饰的对比,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两者的独特风格,从而尝试探讨契丹人与宋人用玉风尚的分别”。但是琥珀艺术之于契丹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因与辽玉的对比,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衬托和体现。
笔者于2003年发表的《辽代的琥珀工艺》一文,主要依据出土材料,对辽代琥珀的具体使用作了分类,并对辽代琥珀的题材、工艺等作了初步的论述和探讨。文章主要将辽代琥珀器分为首饰、服饰、镶嵌和附饰、丧葬用品、宗教用品等几大类。认为虽然契丹人使用琥珀为原料制作装饰品,在其选材上具有独特性,但其题材与中原唐、宋文化密不可分;其工艺,亦多借鉴玉雕。2004年,在《辽代的东西方交通和琥珀的来源》一文中,笔者通过零星的中外文献,以及辽文化圈内出土的域外器物或器物上体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一步论证辽代与中亚、西亚地区存在着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辽代的琥珀原料,很可能来自波罗的海。其路线可能有三条:一是北方的皮毛之路,二是自河中沿古丝绸之路的北线,三是自河中经古丝绸之路的南线。
通过上述研究回顾可以看到,对波罗的海以及缅甸琥珀的研究至晚在19 世纪下半叶即已开始,当时更多的是其生成及成分上的探讨。随着20世纪大量古代琥珀制品的出土,对古代琥珀艺术以及琥珀贸易的探讨逐渐展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更加引发欧洲学者的关注。举办国际研讨会、公布最新发掘成果和研究进展,渐成定制。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琥珀产地的检测和判定技术取得了突破。同时,对琥珀内部所包含的古代生物、植物进行古生物学上的探讨,也是西方一些实验室的专门课题。
中国琥珀艺术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晚期,但多是汉文文献的检索和翻译。真正意义上的发轫,应该是20世纪初劳弗尔的《亚洲琥珀史论》。篇名虽为亚洲琥珀,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中国,而且汉文文献是文章立论的根本。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的探讨,而非琥珀艺术本身。此后将近80年的时间里,琥珀几乎未曾被学术界提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陈夏生将琥珀作为宝石的一种所撰通识性文章的面世。其后90年代末21 世纪初埃玛·邦克、苏芳淑以及笔者的文章,均是围绕辽代的琥珀艺术展开。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辽墓的发掘,使得众多精美的契丹古物面世,其独特的草原风情和工艺成就令人刮目。这些文物是对匮乏的辽代文献的重要实物补充,辽代文化的多角度研究因此在海内外逐渐升温。
虽然,自商始至明代,都有不同时期琥珀制品的出土报道,但由于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材质的器物比较,琥珀制品在数量上很少,所以,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虽有琥珀传世品的收藏,但均被淹没在清宫所藏洋洋文物之中,不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辽代之外的其他时期的琥珀艺术,鲜有文章涉及。笔者通过整理历代考古出土的琥珀资料,加之私人或博物馆的传世品收藏,发现其在数量上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不同时期在使用和题材上各有特色。可以据此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古代西方和东方对琥珀本身的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理解,在工艺方面体现的一些共性,都留下了东西交流的线索。而古代中国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更涉及中国与外围邻国乃至欧洲国家的交通。劳弗尔在其1905年的那篇文章的开头就说,相对所有有助于解决考古学问题的自然产物而言,没有比琥珀更引人关注。因为它涉及古代的贸易及与亚洲的关系等问题。而今距劳弗尔的论述已有百年。在这百年里,考古出土材料的丰富,是劳弗尔那个时代所不能期及的。笔者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契丹琥珀艺术作回顾和探讨,以揭示中西琥珀艺术的特征和异同,契丹琥珀艺术的成就及其内涵,以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本身所包含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期引发更多人对中国琥珀艺术的关注和兴趣,并将之纳入世界琥珀艺术史研究的范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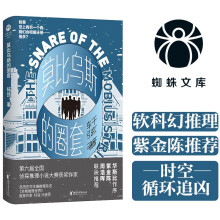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国学大师 南怀瑾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习俗和中国人心理的把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
西方人用汉文写小说(《大唐狄公案》部分篇目有汉文写本),前无古人。
错综复杂的情节,如茧抽丝,娓娓展开,最后才真相大白……它使读者从超凡的逻辑智慧中获得快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石昌渝
他是名士派头的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汉学家……现代西方人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非学术圈里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往往来自《大唐狄公案》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四川大学教授 赵毅衡
“狄公小说是我们从高罗佩博士那里得到的最后的中国公案小说……他的逝世使我们所有侦探小说的鉴赏家们都感到十分悲痛。”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高罗佩逝世的评价
在高罗佩的神笔之下,古老的中国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阿伦·丁·赫宾
如此严格地遵循中国古典文学的风格进行创作,而写下的一切又是如此美妙地使现代读者获得满足。
——《纽约时报》
狄公小说写出了中国唐代的所有魅力、残忍和高深莫测。
——《芝加哥太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