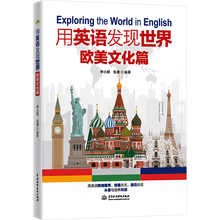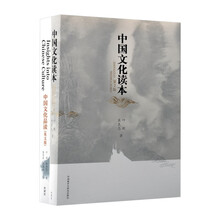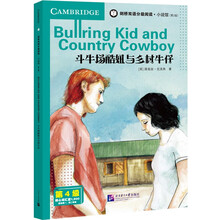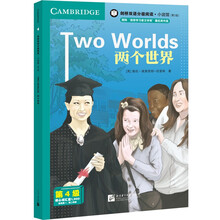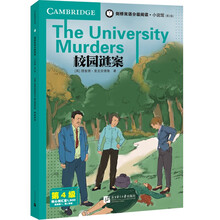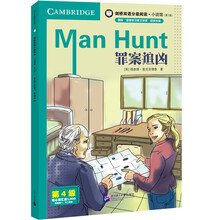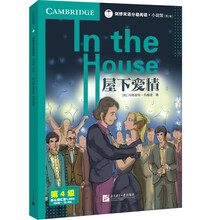他躺在白色的板床上,说:“护士小姐,你能不能……”他又犹豫了,眼里噙满了泪水。他以前也曾这样,在开始问我一个问题时,又改变了主意。我握住他的手,等着他再次开口。他擦了擦泪水,接着说道:“你能不能给我女儿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的心脏病犯了,但只是轻微的。你看,我一个人生活,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他的呼吸突然加快了,我把他鼻氧管的速度调至一分钟八公升。
“当然,我会给她打电话的。”我边说边观察他的脸色。
他牢牢地抓住被单使自己往前挪了挪,脸部的肌肉因过于激动而绷得紧紧的。“你能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给她打吗?”他的呼吸又加速了,太快了。
“我会尽快给她打的,”我边说边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听了我的话,他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将灯熄灭了。我很惊异:在他那将近五十岁的脸上却有一双那么年轻的蓝眼睛。这时的712房间陷入一片昏暗中,只有水槽下面的一盏小夜灯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氧气在他床上面的绿管中汩汩作响。我不愿马上离开,于是就穿过阴冷的死寂来到窗前。透过冰冷的玻璃窗,我看到下面朦胧的薄雾一直蔓延到医院的停车场。“护士,”他突然叫道,“你能给我拿支铅笔和一张纸吗?”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黄色的纸和一支钢笔,放在他床头的桌子上。
然后,我回到了护士值班室,坐在电话旁边吱嘎作响的转椅里。威廉斯先生女儿的情况就填在表格的直系亲属一栏里,我找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并拨通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婉。
“珍妮,我是休·基德,医院的注册护士,我打电话是因为你的父亲,他犯了轻微的心脏病,今晚住进了医院,并且……”“不!”珍妮突然在电话里叫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她又接着问道:“他不会死的,是吧?”“目前,他的状况已经稳定了。”我说道,并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有说服力。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不禁咬了一下嘴唇。
“你千万不能让他死!”珍妮突然开口了,她的语气完全是强制性的,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以致我握电话的手都有些颤抖了。
“他正享受最好的照顾。”我试图安慰她。
“但你并不理解,”珍妮的声音夹杂着恳求的语气说道,“自从我过了二十一岁的生日以后,就没跟爸爸说过话。我们吵了一架,是因为我男朋友的事,一气之下,我就离开了家,我……我就再没回去过,这几个月来,我一直都想回去请求他的原谅。因为,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恨你’。”她的声音嘶哑了,随后竞忍不住大声哭起来。
我坐在那儿,倾听着珍妮的哭声,我的眼里也禁不住溢满了泪水。父亲和女儿,就这样错失了对方。于是,我想到了自己远在数里之外的父亲。想到我曾对他说“我爱你”的话已经是那么遥远的事情了。
当珍妮试着控制住泪水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求求您,上帝,请宽恕这位女儿吧。”“我现在就过去!我会在半小时之内赶到那儿。”珍妮在电话中急切地说。话音刚落,只听到“喀哒”一声,她已挂了电话。
我试图通过整理桌上成堆的表格使自己忙起来,然而我却无法集中精神。
712房间,我知道我必须回到712房间了。于是,我急忙向走廊那端走去,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推开门,看见威廉斯先生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奔过去用手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了。“99号,712房,99号,马上!”在我通过床头的对讲机接通电话总机后,一瞬间警报便传遍了医院。
威廉斯先生的心跳也停止了。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床放平,弯腰对准他的口,给他做起了人工呼吸(一共做了两次)。然后,我又把手平放在他的胸口上,进行起搏按压,一下,两下,三下……我尽量数着,数到十五下的时候我又转而尽全力给他做人工呼吸。
急救人员怎么还不来啊?我只得又开始轮番地进行按压、人工呼吸;按压、人工呼吸。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不能死!“噢,上帝啊!”我开始祈祷,“他女儿马上就要来了,请不要这样结束他的生命!”这时,门猛地被推开了。医生和护士们推着急救设备涌进了房间。一位医生接替我用手按压他的心脏,并在他的口中插入了一根通气管,护士们忙着把药物注射到他的静脉血管。我给他接上了心脏监测器。监测器上什么也没有,心脏一下也不跳。
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着:“上帝,请别这样结束他的生命。
不要只留下悲伤和憎恨。他的女儿马上就来了。让她得到宽恕吧。”“退后。”医生突然喊道。
我把电动心脏起搏器递给医生,医生把它放在威廉斯先生的胸口上,我们试了一次又一次,然而毫无作用,威廉斯先生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死了。一个护士拔下了氧气管,房间里不再有氧气的汩汩流动声。医生和护士们面色凝重,一个接一个默默地离开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呢?我呆立在床边,感到一阵眩晕。这时,寒风携着雪花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外面到处都阴沉沉的,仿佛坠入黑暗的深渊,让人感到寒冷、恐怖。
我该如何向他的女儿交待呢?我忐忑不安地走出病房,只见一位女士正倚在喷泉附近的一面墙上。刚才在712房的一位医生正站在她的旁边,一面跟她说着什么,一面拉着她的胳膊。医生离开后,这位女士的身子慢慢地往下滑,最后跌坐在地上。她的脸上显示出悲痛的表情,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哀伤。显然,她就是珍妮,威廉斯先生的女儿。那位医生告诉了她,她已经知道她的父亲去世了。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带她来到护士休息室。我们坐在绿色的小矮凳上,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她一直愣愣地盯着玻璃罩下那张快被磨成碎片的医学日历表。
“珍妮,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我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这时候表示同情是多么地苍白无力。
“我从来就没有恨过爸爸。我爱他。”珍妮懊悔地说。
上帝啊,请帮帮她吧。我在心里祈祷着。突然,她掉转头对我说:“我想去看看他。”我心想,你何必还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痛苦?看到他只能使你的心情更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