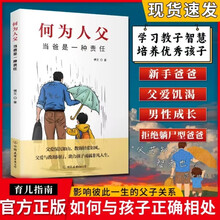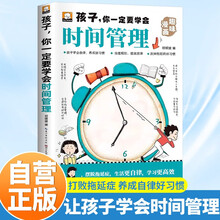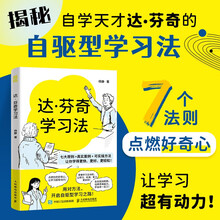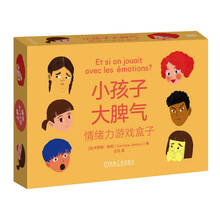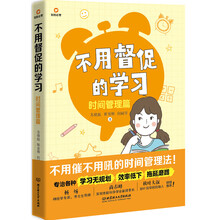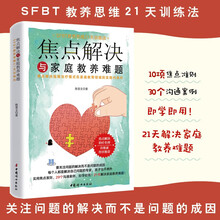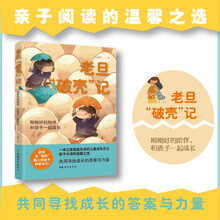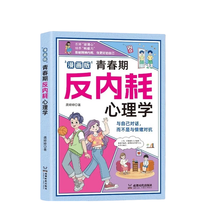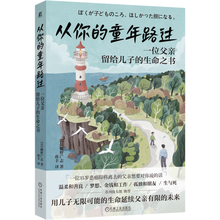一、Orientation 感受哈佛
崇真与造假
哈佛的“崇真”和自由主义在我们看来多少有点离谱。比如历数哈佛传统和家珍,他们不光说出了多少总统,有多少荣耀,也公开“丑闻”和“错误”。
比如哈佛人并不讳言,他们的开山鼻祖,第一任院长伊顿牧师在建校后四年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把收购来的牛肉做饭给学生吃,还私喝供应学生的啤酒。时代不同,地方也不同,咱听了真会吃惊的,感觉伊顿老人家像个难得的清官。
哈佛还有件“丢人”事。1884年,加州有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的儿子去世了,他们想办一所大学以纪念爱子,千里迢迢来到哈佛,向艾略特校长请教用多少钱可以建个大学。艾略特校长看看他们,一脸怀疑地说:“这起码需要500万美元吧。”
艾略特的轻慢不无道理,当时的五百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是个天文数字。斯坦福太太一言不发,脸拉得老长。沉默良久后,斯坦福先生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那就祝福你们了。”艾略特说。
艾略特没料到的是,这对夫妇受了刺激,不仅立志建起用家族姓氏命名的斯坦福大学,还使之最终与哈佛齐名。艾略特卸任后六十年,斯坦福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成为哈佛校长,主政哈佛二十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而且还是哈佛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哈佛在一不留心间,“生出”了两个顶尖竞争名校,耶鲁和斯坦福。斯坦福还在另一点上夺去哈佛不少风光,多年名列美国最美校园第一位。
那对夫妇没有白去哈佛园,他们学习哈佛,赋予斯坦福校园独特建筑风格,所有建筑一律红瓦盖顶,再加上加州独有的西班牙式热带庭院风格。连大学的购物中心,都是花园套花园,说不出是商店,学校,电影院,还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露天休闲咖啡馆。
最重要的是,斯坦福在旧金山湾区南岸带出了人类本世纪最重要的一片园区――硅谷。当哈佛说自己出了最多总统、律师和艺术家时,斯坦福可以说出了最多IT和生物科技精英,他们的毕业生都在驾驶拉动世界科技和经济疾驰的火车头。
哈佛崇真,也不避讳自己曾经“造假”。
“哈佛之父”约翰·哈佛1638年9月去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随着哈佛名声日盛,1882年校董事会决定,顺应越来越多人的提议,给哈佛塑一座雕像。为了美化老人家,他们在学生中物色了一位长相古典的英俊小生谢尔曼·霍尔做模特。
现在,坐落在校园里的哈佛雕像和自由女神像、林肯纪念堂林肯坐像、费城自由纪念馆富兰克林雕像并称美国四大雕像。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无不想在哈佛雕像前留张影,以证明与哈佛的缘分。而第一个利用刚发明的照相术和老塑像合影的正是模特谢尔曼,他说:“和哈佛先生,也是我自己合影,是我一生的荣幸。”
这件事使后来的哈佛人感觉自己也“根不净”。可真真假假,毕竟都是哈佛的历史。“求真”和尊重历史,保护文物打起了架。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让满世界人继续合影,同时昭告天下哈佛也做了假。
我第一次和老哈佛合影并听此“传统教育”,不无惊诧。因为“历史为胜利者所写”,还改来改去。从“名牌”到“有机大米”都作假,人人六根不净,哈佛又何必那么顶真呢?
关于哈佛的“自由主义”举一个例子就行了:
我们自然不齿于“西方民主”,但是走在哈佛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红标语。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都是那里的合法“流派”。
多年前我去哈佛和伯克利等校园,看到街头贴了不少标语,宣告江青死了,悼念“世界革命人民的英明领袖”。那是美国极左翼学生贴的,让我们中国来的“真革命人民”都摔断眼镜腿。
小静邮件:
查尔斯河畔的联合国
爸爸,我真的很遗憾很遗憾!!!你没能来参加开学典礼。如果说圣马科斯是个童话中的贵族城堡,那么哈佛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
今天,我们所有新生都感到自己是公主和王子,因为整个剑桥城的人都在围着我们忙。一早起来,我和妈妈发现已经晚了,急急忙忙去餐厅抓块三明治就往哈佛广场那边跑。餐厅的师傅们都已经见多识广,早早就把早餐和小纸包准备好,因为今天没人会坐下来慢慢喝咖啡。
本来昨天晚上应该早睡些,可是同屋和隔壁的新生,一个是印度来的辛迪,一个是法国的让,一定要拉我去老生的Party。结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谁也不让我半途溜号。一直闹到下半夜才回来。
开学典礼在离哈佛广场不远的主校区。因为学生多,典礼分在许多Hall进行。今天哈佛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街道,广场,校园里到处都是人,而且都是一家一家的。
哈佛的开学典礼就像世界博览会,人群中有的头缠白布,一看就是印度人,有的皮肤很黑,大大小小都身穿大花长袍,像是非洲的酋长。一些像是阿拉伯的女孩穿着西裙,可是她们的爸爸妈妈穿着黑白长袍,还围着面纱。更多的是白人家庭,父亲儿子都西装领带,母亲女儿都穿着漂亮的裙服,听他们的话才知道是美国人,澳洲人,还是法国德国人。
就是看见和我们一样黄皮肤的也不敢轻易认,因为在美国,尤其是在哈佛,见到黄皮肤黑眼睛就断定是乡亲很危险,不光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所有亚洲国家的家庭,你在这里都能找到。
哈佛最难的是停车,除非你停到主校区外。所以我没有车反而是幸运事。学生和家长们,不管是白面孔,黄面孔还是黑面孔,有的从校车下来,有的涌出地铁站口。还有不少私家车停在路边,经常能看见维持秩序的警察彬彬有礼打开车门,母亲和学生下了车,老爹再去找Parking。
有几个衣冠楚楚的残疾学生坐着轮椅从校车下来,司机和乘客都上前帮忙。哈佛不光收残疾学生,而且许多校车都有轮椅升降机。
在整个典礼期间,天上都有直升机飞来飞去。有的是电视台的,有的是警方监测交通的,有的说是载送学生和家长的。我也不知道那是国王还是总统,需要这种保安级别。
不过我相信那天所有家长,包括妈妈都是国王和王后,至少校长教授,接待人员希望家长们感觉是这样。要是世界上有一所学校最礼遇家长,那一定是哈佛。因为他们不仅送来最好的孩子,许多将来会出人头地,而且整个哈佛园,校长官邸和宿舍楼,连同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多数都是家长捐建的。
来哈佛这些天,我已经见识了剑桥警察的彬彬有礼。对哈佛学生,他们永远面带笑容,一口一声“小姐”“先生”,而且有求必应。我们在哈佛感觉很安全,只担心会被警察惯坏了。就是开罚单,听说也得屡教不改,得把他们逼急才行。所以师生们见了罚单一般很不满,而警察给了罚单反倒会很内疚。
今天,连查尔斯河畔的天都格外湛蓝,暗红色的楼群掩映在绿树和蓝天中,不时还有小飞机拉着彩带穿过淡淡的白云。
也许是皮实了,老生说都哈佛的开学典礼从来是一场Show。可是话说回来美国什么不是Show?
街头到处都有乐队表演和盛装“游行”。遍布校区的Hall里有很多酒会和活动。大小广场的典礼现场,有部长,议员,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好莱坞明星即兴表演,发表各种演讲。而哪里热闹,人丁兴旺,也要靠那里的主持人和演讲人彼此竞争。整个剑桥市像个大马戏团,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大会,又像举城节日大喜庆。
冷餐招待会上,有一个身穿花衣服的老先生过来问妈妈和我: Are you Japanese or Taiwanese? 他儿子挺帅的,皮肤有点黑,我开始以为他们是印尼人,可是他们自我介绍是泰国人。我们至少有几次误认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却没人说我们是中国人。这真奇怪,因为哈佛的亚裔学生里,就数中国人最多。
不过和其他Show有一点不同,这里一侧耳朵,就能听到学生和他们家人说希腊语,希伯来语和祖鲁语。我只能听懂法语,其他都是问了才知道的。但是一转脸见到你,大家就会用纯正的牛津音和美式英语热情交谈,好像我们都已经在哈佛很久,认识了半个世纪了。
参加开学典礼让我有种很强的感受,一种归属感。你会感到,这就是哈佛,世界的顶尖学府,他们都是你的校友,你的共同家长了。你是和未来的泰斗,领袖,总统在一起。你真的已经属于这个整体,成为哈佛成就,光芒,传统的一部分。
回件:
燕京图书馆和北大清华园
小静,我也很遗憾没能参加你的开学典礼。不管是对一个为你感到骄傲的父亲,还是一名经常告诉你要用新奇渴望之眼观赏世间一切的老记者,这或许都是个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你已经是哈佛人了,像其他哈佛前辈一样,从今天起,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你说的哈佛园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亲切。第一次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我要求访问一些地方,白宫,收有独立宣言的国会图书馆,纽约渃顿出版社,蒙大拿州的农场和重罪犯监狱,也包括你邮件里说的燕京图书馆。
美国中文藏书最多的当属国会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甚至义和团的灭洋檄文和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小报,只要能收集到的印制物,他们都保存,视为文化历史的一部分。那里能看到许多在中国都看不到的东西。
这不光和哈佛的理念有关,也来自我们鄙薄的殖民地文化。去香港我总有一大享受,随便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十多个国家语种的电视节目。
殖民地是处女地,所以虚心接纳所有宗主国的文化,百年下来,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香港成为亚洲明珠,而自大的日不落帝国和我们的泱泱之国反倒落后了。
燕京图书馆和最初名为“燕京大学”的北大差不多是“同时代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清政府支付巨额赔款。列强中只有美国把钱又拿回来,帮助中国办文化教育,建了“燕京大学”,“清华园”,还有协和、同仁等一批大医院。
中国第一批漂洋过海去哈佛的“公派留学生”,用的也是庚子赔款。只是他们乘坐的是木帆船,脑后挂着大辫子。竺可桢、杨杏佛、赵元任、林语堂、梁实秋,都是早年留学哈佛的。
不仅燕京图书馆收藏每一本到手的中国典籍,哈佛除十个研究生院,两个本科学院外,还有一个专门研究中日韩等国文化和历史的东方研究中心。你要是对自己的历史感兴趣,可以去那里补补课。有关中国那段历史的材料,现在不光美国人,连在中国,也很少有人能看到。
中国风筝和花木兰
你还记得小时候在西雅图,我去你们学校讲中国风筝吗?
后来我才发现,最先进最漂亮的风筝在美国商店里。Pizza 从意大利传入美国前远没有那么好吃,神灯是阿拉伯的,花木兰是中国人,但是迪斯尼把它们变成动画风靡了世界。
如果说哈佛真有某种一言道明的精髓,那就是兼收并蓄中的创造,不管是肤色各异的学生和教授,还是汇聚传承的文化。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说的“虚怀若谷”和“江河下百川”。
有一次我去广州美国总领事官邸听音乐会,美国歌手把中国民歌改良创造,加了和声和变调,节奏也更明快,既惟妙惟肖又耳目一新。那个三两人的小乐队在中国巡回演出,音乐学院礼堂走廊门口都挤满了听众。
美国人像不安分又爱捣鼓的魔术师,学问,艺术,技术,只要丢进布袋,出来就是一片新风景。
哈佛中心广场也是My favorite,我在露天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喜欢看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根据他们肤色年龄身高和长相,猜测他们是哪国人?干什么的?信仰哪种宗教或文化?
中国现在也很讲国际化,北京上海的外国人也很多,可是唯有在纽约,在拉斯维加斯,在哈佛广场,我才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身在电影中的古罗马,一个财富文化交汇的帝国中心,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