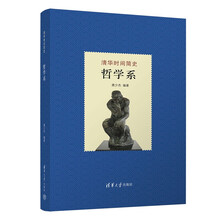就应然层面而言,教育的本真是成就人和发展人,回应并满足受教育者生命成长和人格发展的需要。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类型中,“人”的构成、“成就与“发展”的内容和标准存在重大差异。承认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接纳某种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而是要表明人类共同性的教育理想与差异化的教育实践之间的冲突。在公民社会中,人的理解不仅突破了臣民时代范围的有限性,而且实现了相互之间形式上的平等性;教育的本真具体化为将生物意义上的单独个体培育为社会生活实践中完整的现代适格公民,使之重理性而不失情感、求自由而不失美德、崇权利而不失责任。这就使得它本质上区别于臣民社会中的教化因为臣民社会的权力关系与权利结构使人“单向化”,使人成为特定社会阶层所需要的“被肢解”的存在,教育的重点不在“育”而在“化”,其功能被异化为控制人和驯服人的手段。
诚然,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有着为人和为己的双重使命。但是,在臣民社会和统制社会中,教育为人的维度被凸显,而其为己的面受压缩。在这种教育思维中,教育存在的价值主要不是实现个体“是其所是”的生命成长与人格发展的潜能,而在于驯化为满足特定的权力集团治理社会所需要的便捷工具。尽管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及与之相随的政治生活变迁为教育的回归提供了有利的时空契机,但是,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习惯,对当下的教育实践仍有着潜在的、根本的和特殊性的影响,使之成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而极有可能被借鉴为跨越时空的现实教育资源,甚至由此沦为社会进步的阻滞性力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