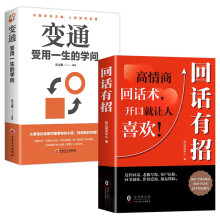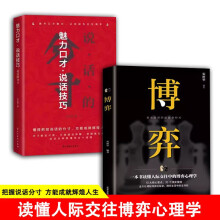一般说来在不利情境中,越是带着自我保护色彩,后果就越不严重,幽默的成分就越多。这种特点在日常交往中更能看得出来,因为日常交往的情境一般并不像见到皇帝和法西斯的秘密警察那样严峻,人们有更多的情感自由天地以充分的幽默感来进行自我保护。
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卖乌龟的人吹牛说他的龟是万年龟,能活一万年,一个孩子买了回去,第二天就死了,孩子便去责问。卖龟的答道:“噢,昨天我忘了告诉你这乌龟到昨天为止,刚好活了一万年。”还有一则笑话说:某人想买一只钟,他问老板:“你店里挂的几个钟指针所指为什么各不一样?”老板答道:“如果所有的钟指的时间都一样,你怎么能区别哪一个准确的呢?”这两则笑话的共同特点是所答皆带有很大的诡辩色彩,并非属于严肃的理性思维。人人所欣赏的不是他的急中生智的那种智,因为那种智明显是一种“歪理”,歪理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如果要执著于逻辑的理性,那么小孩可以追问:你怎么知道那乌龟到昨天已经活了一万年的呢?或者,你如已知道,而在成交时不加说明,是不是一种欺骗呢?而时钟店的顾客也可以对店主说:这只能说明你店里的时钟只有一架是准的,其他都不准。如果这样,就没有幽默感可言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依理性逻辑交谈,而是在表现一种超超了这种逻辑的情感。人们不会傻乎乎地死揪着店主所说的话中那么多显而易见的漏洞不放的。如果揪着不放,那就是不懂幽默之妙。
通常许多人之所以缺乏幽默感,不懂幽默之妙,首先是他在不利的境遇中常常陷入精神的被动,不能以轻松的心情来自由变换自己的情感的视角,总是被习惯的实用价值所困,所以情感不能获得自由。其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幽默感的人常常心眼儿太死,死守着通常的理性逻辑不放,不懂得我国民间艺术家的宝贵经验:“理儿不歪,笑话不来。”自然,歪理有时会坏事,如果你把它当作森严的理性逻辑来使用,只能把人们的头脑搅乱,但是歪理也有歪理的用处,那就是用于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用于自我的情感调节,使自己在不利的境地中精神上轻松起来。
当然,幽默并不完全是用来自我保护愉悦情感的,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带着攻击性的。不过这种攻击在形式上是软性的,不像一般讽刺那样尖锐,那样狠。传说一个美国百万富翁在左眼部装了假眼,与真眼无异,有人恭维他说:“你的左眼比右眼更像真的。”一次他让大作家马克·吐温猜猜哪一只眼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在左眼说:“这只是假的,因为在这只眼里还有一点儿慈悲。”这样的回答,既有攻击性也有幽默感,但二者相比,其攻击性较强,其犀利的锋芒更甚于情感的幽默。由于这里突出一个鲜明的思想观念——资本家是没有慈悲的,鲜明的思想观念越占优势,幽默的意味就越弱。有一个年青的科技工作者对爱迪生说,他要发明一种溶解一切物质的万能溶剂。爱迪生吃了一惊,答道:“那么你打算把它放在什么容器里呢?”这个回答的妙处在于机智地揭示了隐藏在对方思想中的矛盾,这就完全符合理性思维的规范了,因而便很少有歪理的意味,也就很少幽默的意味了。
要使幽默的意味增强就得弱化这种纯粹的理性色彩,也就是将攻击性弱化,即使不能完全弱化,至少也要避免直接地表述,而用间接的方法,与柴可夫斯基同时的俄国著名作家、钢琴家鲁宾斯坦,有一次在巴黎举行演奏会,获得巨大成功。有一个惯会卖弄风骚又很吝啬的贵妇人对他说:“伟大的钢琴家,我真羡慕你的天才、可是票房的票已经卖光了。”鲁宾斯坦很了解她的这一套,当然不想给她票,但是他没有直接拒绝,因为直接拒绝的攻击性太强,锋芒太露,有损于幽默的效果,他采用了把拒绝间接化的方法。他平静地答道:“遗憾得很,我手上一张票也没有。不过,在大厅里我有一个座位,如果您高兴……”贵妇人大为兴奋问:“那么,这个位置在哪里呢?”鲁宾斯坦答:“不难找——就在钢琴后面,”这样的座位自然是属于钢琴家自己的,对于贵妇来说是毫无实用价值的。但是由于这个拒绝是间接的,直接语义上的同意提供座位和间接暗示的座位的虚幻性形成反差,造成了怪异之感。这种怪异产生于心理预期落空,于是便产生了笑,这一笑便使情感从紧张中得到了松弛。
如果你要强化你的幽默感,你就要把针锋相对的矛盾淡化、间接化。即使无法消除其中的攻击性,也要尽可能让读者去领悟体验。如果你要强化你的智慧,你就得尽可能用逻辑去征服人,那就不要怕攻击性,甚至讲出一些格言和哲理来,例如有一则故事:富翁问学者:“为什么学者常登富翁之门,而富翁却很少登学者之门?”学者回答说:“这是因为学者懂得财富的价值,而富翁总是不懂得科学的价值。”当然,为了尽可能带上一点儿幽默,可以用庄重的语言来讲一些与之不相称的事情。例如,丘吉尔说:“我最辉煌的成就,是我竟能说服我的妻子嫁给我。”这句格言式的警句由于大家都知道丘吉尔在政治上的成就而显得幽默。如果有一个人对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一无所知,那他就不可能享受到丘吉尔的幽默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