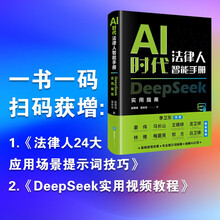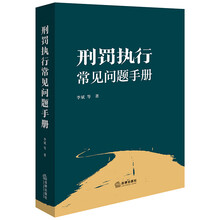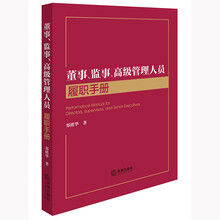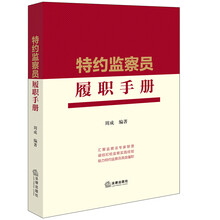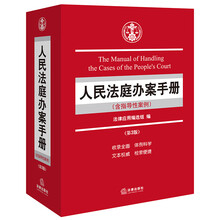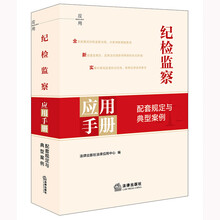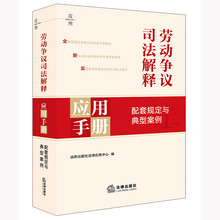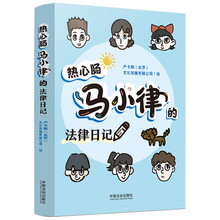实务当中的前述做法可谓绝对主义刑罚观在审前羁押活动当中的具体影响。殊不知绝对主义刑罚观亦具有极强的副作用。因为,绝对主义刑罚观认为:人类是具有理性、良知的动物,对于是非善恶应有分辨能力,对于社会、他人负有不得侵害之义务。若违背此项弃恶从善义务,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就应对其加以制裁惩罚。犹如宗教之间因果循环报应一般,杀人者下地狱,此乃天经地义的惩罚原则。“以命偿命、以眼偿眼”这句《古兰经》上的圣语是绝对主义刑罚观绝好的明证。此种刑罚观在法制初创时即有体现,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骨,则折其骨。”古罗马森然矗立的铜柱上亦有同样肃穆的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人和解者,则他本人亦应遭受同样的伤害。”
绝对主义刑罚观在实务当中强调刑罚的“溯及既往”的惩罚功能,无视“毖后”的预防功能,并单纯以惩罚为目的,表现为重刑主义,具体表现为严刑峻法,甚至使用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方式。而单纯的为罚而罚,实质上是对刑罚预防功能、改造功能的忽略和抛弃,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及回归社会;而相对主义刑罚观则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获得的快乐与满足,最终使人们畏惧刑罚,不敢触犯刑律”。因此,作为相对主义刑罚观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而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虽然贝卡利亚主张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统一,但他更为强调的还是一般预防。另一位相对主义刑罚观的代表人物——英国法学家边沁进一步丰富了贝卡利亚的思想,他认为刑罚只是一种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对于犯罪来说制裁不是唯一的,补救的方法应当是多元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