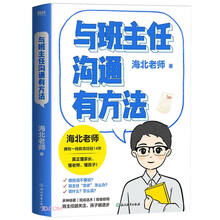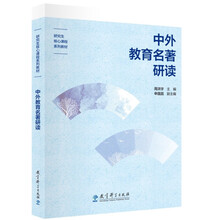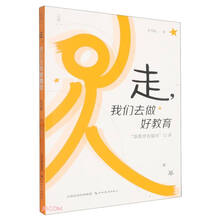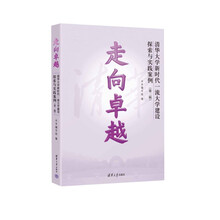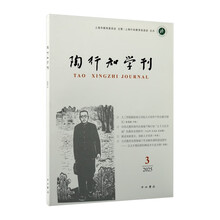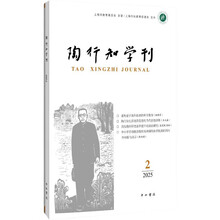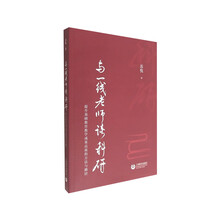常把自己带进课堂
语文课上得单调沉闷,我以为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见书不见生活;见书不见人;见书不见情。这里所说的书是指教科书及教辅资料,这里所说的“生活”“人”“情”,是指在那些心中只有应试的教育者看来无它不为缺、有它无大益的东西。但一个睿智的教育者心中装的更多的是生活、人、情,而不是分数。如何让语文课堂中有生活有人有情,途径和方法是多样的,但我以为教者把自己带进课堂不失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
讲课时,是免不了要举例要引申要旁征博引的。这样做时,老师们往往习惯于在名人伟人的经历、言行中找帮助。这“找”中很有一部分就是舍近求远的自找麻烦和浪费资源——其实,从你身边的人或你自己身上就能获得帮助。
著名教育家于漪先生在她的一篇文章(载《人民教育》2004年第7期)中讲述了她教《最后一课》时的某些环节。她说,她在学生朗读和讨论后向学生讲了自己在抗战时的一段亲身经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人,家乡的小学即将解散,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教师用‘心’唱歌,唤起了我们幼小心灵的觉醒。从此,这首歌不断在我胸中激荡,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于老师说,她讲的时候,学生都屏息凝神,仿佛他们都走进了50多年前的那所小学中。这堂课就是因教者自身经历的介入,而掀起了师生情感的高潮,成为这堂课的亮点之一。
笔者在课堂上从不吝啬于向学生交出“自我”,且深深体味了这“交出”后的好处:作为一个身有残疾的教师,在讲海伦·凯勒、奥斯特洛夫斯基、史铁生的文章时,我总是不忘向学生讲述我从这些作者身上所获得的力量以及他们对我人生的影响。每接手一届新的学生,在向他们讲鲁迅时我都要向他们讲到我1989年去上海鲁迅故居参观时,受到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奚落的情景。那天,我好不容易找到鲁迅故居所在的那个胡同,在胡同口坐着一个卖西瓜的青年。那时,我口渴了,就坐下来买西瓜吃,准备歇息一下让精神恢复后以几分奕奕神采去拜见大师。小伙子见我是外地人,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说:“从湖北来的。”“从湖北来上海做什么?”“参观鲁迅故居。”“你大老远地从湖北来就为了参观鲁迅故居?!”他一脸惊讶,瞪着眼像看一个怪物。“是的。”我点头。他接着不断地摇头:“就几间空房子有什么好看的!鲁迅值几个钱?现在的正经事就是如何挣钱,挣钱了去国外,这就是前途。”我没想到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竟然这么健谈,更没想到我在鲁迅的家门口受到了这样一番教训。我向学生讲述这番经历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对拜金主义世风盛行的忧虑,是为了告诫学生:人不能只为物欲活着,一个不懂得尊敬和缅怀伟人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在上《送东阳马生序》时,我也讲到了自己的一番经历。我说:“我父母都是没读过多少书的农民,家里根本没藏书,而且很穷。嗜书的早期,与宋濂一样,书都是借来的。跟宋濂不同的是,我并不是每本书都还的——估计借主是个不在乎书的人,只要他不讨要就不还了。至今我的书柜中还有好几本这种借而不还的书。”我说:“我曾几次到山上砍柴卖给村里的窑场,换了钱后去买书,曾几次到沟或塘里打鱼卖了后去买书。”我说:“我当民办教师时参加了中文专科函授学习。暑假时到市里集中面授,为了节约每晚2元的住宿费,我好几次拿了几张废报纸铺在教学楼楼顶上睡。早晨起来,发现身上到处被咬得斑斑点点,为城市饥饿的蚊豸贡献了不少的美味佳肴。”名人伟人们爱书惜书勤学苦学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我觉得都不如我自己的现身说法来得有效。我自身的这些事情肯定给了学生更真实更感性更亲切的感受,他们听起来更容易感动也一定更难忘。
前不久,我在上胡适的《我的母亲》时,讲到了我母亲的性格和品质以及她对我的深刻影响,讲述了我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还向学生朗读了我自己回忆母亲的一篇散文。当我朗读到我母亲临终时使劲捏着我的手对我嘱咐时,我哽咽了。我停住,想让感情镇静一下后再继续往下读,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讲台下的一片哭泣声……
赞科夫在他的《和教师谈话》中提醒老师们:“不要忘了学生本身的生活。”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同人:“不要忘了你自己的生活。”在课堂上向学生交出“自我”,不仅为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提供了真实可感的例证,也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了解老师是每个学生或显或隐的内心愿望),也滋生了学生对老师的亲切感(这是一个师生心灵融合的过程,可能从此你就被学生视为一个可以与他们交心谈心的朋友了),更重要的是——让课文的人文教育功能在教师的现身说法下体现得更为充分。
每个教师的经历不同,人生际遇各异,因此适合向学生交出“自我”的场合也各不相同——有的适合在这堂课上交,有的适合在那堂课上交,但总有需要你把自己交出去的时候。尽管每个教师身上都不缺少这种利用起来很方便的资源,但这种资源在每个教师身上肯定也存在量与质的差别。量的多少和质的优劣,就取决于各人的人生经历和人格力量的状况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