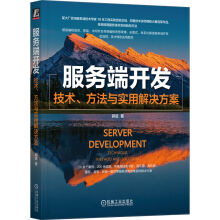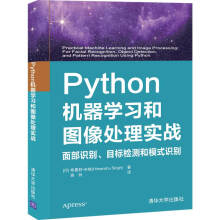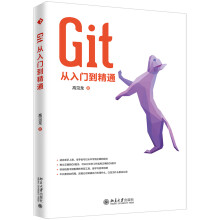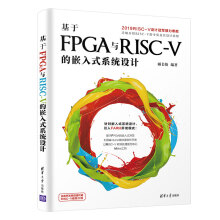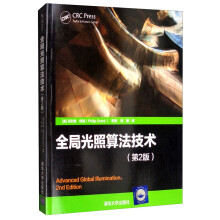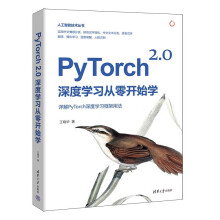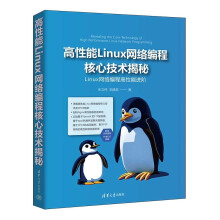问题还没完,就算厘清了三珠钗与马刷子,也并不能维护花钱的“纯洁性”,剩余的“花钱”们就能保持纯洁了吗?显然未必,所谓纯洁性,无非是说,这些物件,既非行用钱,也非其他明确的日常功能物件,是纯粹的戏作,那么符合这样的纯洁性条件的物件有多少呢?其边界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花钱的分类与功能,可涵盖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吉庆、卜卦、殉葬、赏赐、凭信、镇库、纪念、祝寿、挂灯、上梁、系包包袱、镇水、性教育等方面。看官,这些“花钱”,有的是冥葬工具,有的是延命符牌,有的是古代棋子,有的是行酒筹码,有的是帮会信物,有的是宫灯挂坠,在花钱这个“机构”成立之前,他们大多都是有自己的“就职单位”的,只是现在都兼了“花钱”的第二职业而已。没有生下来就为“花钱”这个目标而制作的“物件”,除非各类善意或恶意的臆造、戏作及仿造品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珠钗也好,马刷子也好,这样的发簪功能、马具功能并不是阻挠他们加入“花钱”俱乐部的必然障碍,而是说,其不具备圆形钱型等外在条件,使得他们进入“花钱”系统缺乏了必要性,但是这点也不是科学的,非钱形的“花钱”多了去了。问题是,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条件约束限制,花钱队伍真的要无穷扩军而最终无所指向了。
假设承认花钱从整体上说是第二性的物件(即各自本有属性与功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其外延加以约束,这个外延,大致分为钱形(主要是圆形方孔系统)、非行用、佩挂、铜质四大属性,这四大属性,并不是四个必要条件,而只是四个参照系数,花钱判断依据的模糊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不同的历史阶段,花钱的工具性与游戏性有不同的阶段性侧重。中古之前,以压胜为代表的花钱,多有明确认真的宗教作用;中古之时,从娱神到娱人的转折阶段,大家在信奉神灵的时候不免带了点半真半假,这个时候,玩耍的成分已经逐渐起步:到了清代,除了上梁、冥葬、帮会凭信等少数类别外,花钱多多少少都带有轻松玩耍的气质,即使花钱上面写有“连中三元”、“五子登科”,也不能断定这个就一定是秀才考试的专用“护身符”,也许丫髻蒙童就已经开始佩带这种挂件了,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美好祝愿而已,比如,现在的出租车上挂个带领袖头像的平安牌,我们相信,这个即使是美好祝愿,也是有具体功用的,但是在瓷杯上有“中华腾飞”四字,我们不妨称它为美好祝愿,或时代口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