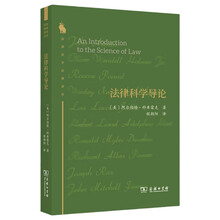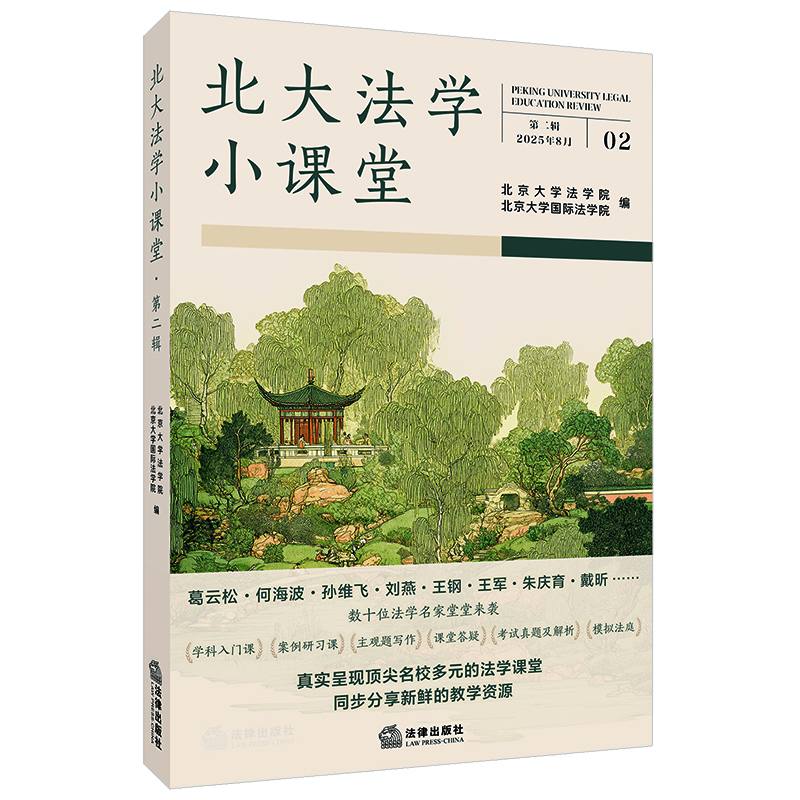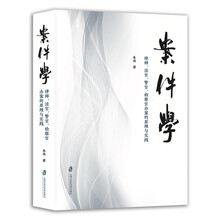第一辑 随笔序文<br> 学术的偏执与忠诚<br> 或许是这些年来,人们的日子过好了,素质也提高了,谈论学问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昔日学自官出的旧习日渐被学在民间所取代。无疑,这是吾国社会进步,人民向往文明的必然表达;也是以文字为代表的符号一旦深入人们的心灵世界,所带来的必然回应。同时,谈论学问的人之所以如此之多,也和我们固有文明对学问的关切、崇尚不无关联。尽管在国史中,帝王们导演的焚书坑儒、文字陷狱等惨案不绝于书,但或许是受“学而优则仕”的感召,或许是因科举取士制的熏陶,读书人、学问家的地位在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即使不是最高的,也是相当令人尊崇的。学问家们很少因为自身的受难而遭民众的普遍唾弃。<br> 在鄙乡那个偏僻之地,即使再穷、再没文化的人家,也喜欢附庸风雅,在自家主屋挂上几幅字画。特别是,倘若那字画的作者在当地还有些名气,则人们的谈资每每由字画而及字画的作者,于是懂字的还是不懂字的,都会津津乐道;知作者的还是不知作者的,都会谈笑风生。记得鄙人小时候,尽管村民们往往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对娃们能初中毕业,或者最好能上个高中,都充满期待。这种情况,自然绝非仅存在于鄙乡。200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鄙人到贵州调查,在湘黔边界的深山大沟里,在叶辛笔下那“高高的苗岭”上,在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不仅藏有数万份康熙以来的契约,而且那契约书法之精美,令人叹而观止。直到如今,当地村民能“舞文弄墨”者仍不在少数。为此,鄙人将在当地成文的一首小诗,交由一位姜姓村民书写,如今,这幅书法作品就挂在我在威海的家壁上——“头枕清江问世川,波声对破夜阑珊。桃源小令今何在?残月朦胧云水间。”。<br> 现在,吾国终于有条件让更多的人关心学问,摆弄学问了,但学问之路,尽管读大量书是必要的,但充其量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读书之外,对社会万象的观察,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必要对照与有机结合等等,都应当是一种超群绝伦的学术观点提出和深化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正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那样,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多少有一些偏执。尽管偏执这个词是一般人不大欣赏的,但在人文一社会学科中,对认准了某一领域、某一观点、某一主张的学者而言,坚守偏执的立场,锲而不合,刨根问底,终会有所建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偏执并非学问的天敌,甚至是深化学问的一种必要态度和立场。这才能导致所谓“片面的深刻”。反倒是那种左听听也有理,右看看也有理,学术立场摇摆不定,学术见解左右游弋的人们,指望其做出什么新鲜学问,可能真是勉为其难了。因为他们不会执一己之见,下勘检功夫;因为他们耳根太软、眼界太浅。<br> 吾人曾有如下有关智慧之分类:学术智慧不同于决策智慧。前者着眼于攻其一点,尽管不能说不及其余,但只有和这一点相关者,才堪引用,’否则,就可能文不对题,甚至离题千里了。基于此,完全可说学术智慧所崇奉的就是“片面的深刻”。学术上的多面手,如张衡、郭沫若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固然存在,但并非是一种常态。<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