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博克(Derek Bok),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和实践家。1971-1991年任哈佛第25任校长,任期长达20年,在任期间致力于哈佛大学课程改革,将效果不佳的通识教育转为课程教育,奠定了现代大学的课程标准,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公认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也是近50年来,任期最长的哈佛校长。退休之后,博克并没有隐居乡里,1999年,博克就任美国国家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研究美国政府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应发挥的作用和合理的方式。离任15年后,他再次重返哈佛于2006-2007年间担任代理校长,接替因歧视女研究者言论辞职的校长萨默斯。博克也因此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唯一个两次担任过校长的人。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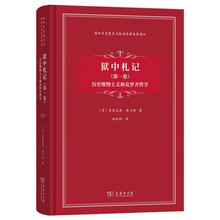








——《撞上快乐》(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
博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样的政策能够给民众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并将其对政治学的真知灼见与新近的幸福研究融合起来,给出了大量惊人的解答。
——《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作者、英国政府经济顾问 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
到目前为止,这本著作在幸福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观点公允、实事求是、见解深刻。德里克·伯克没有从追寻幸福研究的意义中退却,而是敢于直面并拓展幸福研究的最新成果。
——《幸福的历史》(Happiness: A History)作者 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McMa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