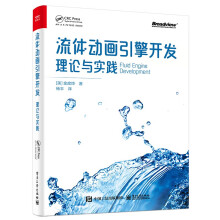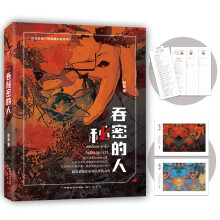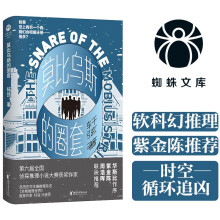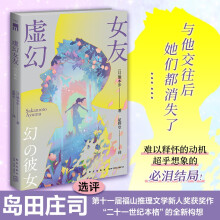过去有许多学者以一年为题出版专书。有些用无关紧要的一年为题,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有些则是讨论关键的一年,只是对关键年代的看法不同,如战后关键的年代有认为是一九四七年,有认为是一九四八年,有些认为是一九四九年。。然而战后任何一年都可能是关键的年代,如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在接收上出现许多弊端,复员工作不力,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民怨,一九四五年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年代。因此战后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转折或关键的年代。
在这些年代中,一九四九年是最被关注的一年。有些学者如傅国涌以知识分子为题,有学者如张仁善写当时的中国社会。而且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意义,两岸学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大陆学者田居俭谈到:“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基的一年。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此期间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造成斯后半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实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当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梁漱溟本来希望不要有“成王败寇”的观念,但当时确有许多人基于现实来评述国共的战局,将战争的责任推给国民党的腐败。一九四九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的年代,一个角落正在逃难,一个角落正在庆祝,更多的地区可能一如往常,很难以一个画面涵盖所有的事实,本书希望以大迁徙作为探索的重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