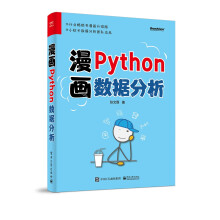穿和服的女人
我所在的城市,有家日本料理店,门口站着四个穿和服的女子招徕客人。也许是工作时间太长了,累了,站得歪歪斜斜,和服的大领子也歪到一边了,甚至一侧几乎滑出了肩膀,乍一看,倒恍若风尘女了。
穿和服是考验人的。韩国学者李御宁说日本文化是“包袱皮文化”,不像西方的“皮箱文化”。皮箱是立体的、把人装起来的,因此也有了把人端起来的功效,比如西装。而“包袱皮”是随形而变的,和服就是典型。《魏志·倭人传》这样描绘最初的和服:“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不“量体”,那就是考验你的“体”了,看你的身体能否像衣架一样把它撑起来。
所以日本女人需要经过仪态训练。未成年的女孩子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她们是未雕琢的玉,从她们身上,难以看到她们母亲的模样。
但是到她们成年了,就要训练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比如走路不能左右摇晃肩膀和腰肢;站立时必须五指并拢,两脚丫的开角应该是六十度;坐时要两膝并拢,不能叉开,更不能跷二郎腿,手要自然放在大腿上,臀部适当往座位深处坐,腰部虚倚椅背……如此讲究。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电车里,日本女性端端正正坐在座位上,两腿并拢。现代女性往往喜欢穿紧窄的短裙,只有这样坐,才不会走光。她们还把随身带的包压在大腿上,把仍有走光危险的三角区压住、遮挡。无论多久,她们都会保持这样的姿势。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中国女性很可能坐得懒散,两腿不经意就叉开了。并非对自己国家女同胞有偏见,只是就事论事。
也许国人仍会不舒服,说,不就是端庄吗?咱们传统也有,日本人,还是从我们这学去的,和服也是我们的唐装。可惜我们已经没有了,总不能硬着嘴说“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吧? 中国人看世界,往往犯错误:面对人家好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祖先早就有了。而在看日本上,还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你不过是搬我们的,我们很懂。但其实恰恰对日本,我们很不懂。比如对日本女人,在电车上,一个女子确实很端庄、稳重,但如果你跟她搭讪,她立刻会显出被惊吓的神情。这种神情,在几乎所有日本女性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包括年届八旬的老妇,有的还伴以“元——” 的惊讶声。(如今这语气似乎也流传到中国年轻女孩子这里了。)这并不是真的被惊,真的被惊,声色不会如此动人;这是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肯定有假,她们完全可以不惊的,这惊,只是为了显示天真、不更世事。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女人和小孩难养”,在这里倒似乎得到了佐证。在日本,女人和小孩常被归为一类,她们跟小孩一样幼稚,所以丈夫对妻子说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神情,甚至是不耐烦的教训。而女人也乐于承认自己无知,做出惊惊乍乍的神情——与其是惊异,毋宁是挑逗;与其是无知,毋宁是乞怜。
和服虽然源自中国唐服,一样的高腰、长裙、斜襟、宽袖,却跟唐服有着微妙的区别。它端庄,但又形似亵衣,柔软、大开领,无论是留袖、振袖、小纹,甚至是豪华的十二单衣,乃至有着神圣感的洁白的结婚装,一种端庄之下的放任。我曾说,和服把日本女人穿得像一朵花。此刻我忽然想起深作欣二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华之乱》。和服给人柔软而凌乱的感觉,让人想到暖昧的被窝,甚至引发被撕扯、被蹂躏的联想。即使是肃穆的丧服也有两面性。《失乐园》里的凛子就是穿着一身丧服,从父亲的丧礼上偷偷溜出来,跟婚外情人幽会的。情人久木企图跟她做爱,她抗拒,但她爱他,想满足他,于是她不脱丧服,为他用特殊的方式做了。在这里,穿着丧服的凛子把肃然和冒渎、强迫屈服与自愿奉献融聚一身,令人不忍目睹,又心旌荡漾。不像我们的《黄金甲》,只知道把唐装里的奶挤得爆爆的,整一个无脑的大奶痴。中国人的艺术感觉和日本人的艺术感觉,在这里见了分晓。日本人重的是暧昧的感觉,端庄是表,风骚是里,是一种“闷骚”。
即便是风尘女,也是“闷骚”。日本许多时代剧里的风尘女,喜欢一拍熟客屁股。这种拍熟客屁股的细节,虽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中国也有“打情骂俏”之说,虽然都属于挑逗或者卖嗲,但在日本这里,更有着暖昧气味。这暖昧不止是:咱们是关起门来的一家子;还有:我不更事,比你傻,你可要让我哟!外国人是难以体悟其中之妙的,包括美国人。我曾说,虽然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但是中国跟美国倒离得近。对美国人来说,了解日本人,也比了解中国人难得多。所以在拍《艺伎回忆录》时,美国人导演罗伯·马歇尔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让三个中国女演员演日本艺伎。单凭章子怡那瞪人的眼神、巩俐那豪迈气、杨紫琼那个硬朗,就满是中国风味,即使她们穿上了和服,也是中国女人穿上和服。毕竟,她们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甚至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土壤里成长出来的,引用日本男人的说法:“中国の女性,强!” 似乎罗伯特·马歇尔至今没有醒悟,毕竟,西方人看东亚人,个个反正都那么回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