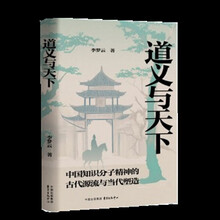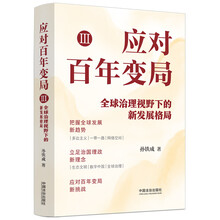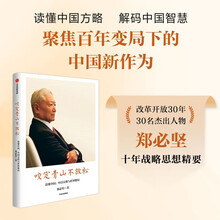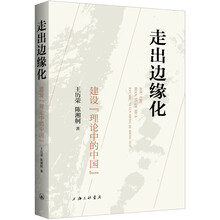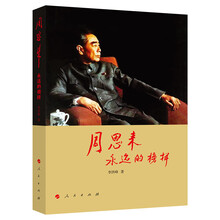在李普赛特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巩固”一一取得更广泛、基础更深入的合法性,使民主能够难以撼动地扎根并被无可置疑地期待能够持久——包括两个挑战:既从工具性上又从自身内在本性上确立起对民主的承诺。绩效的有效性——这对李普赛特来说主要是指“持续的经济发展”——建构起了一种工具性,而合法化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它要求新的民主能通过谈判以不过于激进地威胁“各主要的既有体制的地位”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政治的变迁,从而在关键的转型时期,特别是在组建并向新的社会阶层和政治人物授权时,能够保留以往体制某些象征物的延续性。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行动,既要应对那些正在失去主导地位的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又要赋予新的社会和政治群体(外来者)足够的通道以获取权力,使他们能集合在一起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种平衡和对妥协的需要,后来在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米特关于民主转型的迄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也有所提及,他们强调了在政治对手或公民社会的威权精英与民主力量之间进行正式或非正式谈判、相互妥协、相互理解并达成政治协定所具有的价值。
李普赛特在其早期著作和后期文章中都强调了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使某个社会的基本政治或社会条件仍然挑战或不能迅速断定民主作为该社会最好的政府形式所具有的内在的合法性,但只要民主体制能够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持续的物质进步,人们也有可能接受这一政府形式。但在缺乏深层价值维度也就是内在合法性的情况下,人们对那种物质进步的支持总是有条件的。最稳定的民主政体无疑是那些既有内在合法性,也有长期有效性记录的体制,而最脆弱的民主政体则是两者都不具备的体制。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体制,一些新的民主政体(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共和体制),唯有或主要凭借他们的绩效也能赢得支持,但大萧条一来临,它们的支持就立刻土崩瓦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