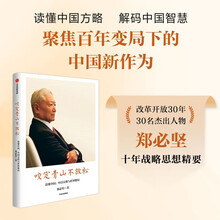这是八条僵黄的蚕,静静地被覆盖以八张软沓沓的桑叶,白色的桑叶,没有水分,和那八张被岁月抽干了水分的脸一致。
这是一间方正的病房,分两排,整齐排列着八张床。床上的八个老人中,两个年逾九旬,六个八十多岁,最长的已经在这里躺了七年。
白被子底下是他们扭曲变形的身躯,尿屎都不自知,全靠护工料理。一个面相厚道的女护工,端着脸盆进来,冲我笑着打个招呼,麻利地掀开被子,戴上塑料手套,蹲在床边,为一位老人抠大便。“这八个都归我一人管,每个都得这样。”她笑笑,像说今年天寒菜价样样都贵一样。病房外面正是北风呼啸,楼道里不时有医护人员和探视家属经过,这间病房里却格外安静。靠窗的那位仰面平躺,紧闭双眼,嘴巴却大张着,一动不动。他隔壁那位,头侧歪着,眼睛空洞地大睁着,犹如两口枯井。
床上的所有人都不露手足,他们如同一条条断了桑叶的蚕,鼻子里那根乳黄色的管子,是维系生命的唯一通道,比风中的蛛网还脆弱。
扭转身,你被吓了一跳,居然靠门口的那位在动,他笔直仰躺着,眼睛茫然地瞪向天花板,一只手却从被子下慢慢伸出来,缓慢摸向床头柜上一个小塑料盘,一个包子被他摸到手里,又极缓慢地送向嘴边,他开始用没牙的嘴咀嚼包子!
枕畔,是一个婴儿用的奶瓶,里面有半瓶水。
另一间病室,只有三张床,一位老太太靠墙坐着,黑棉裤,灰上衣,罩着拉绒深灰马夹。被子没叠,散乱地堆在身边,上面赫然放着一根黑漆拐棍。另两个床空着,一个被推到楼下散步去了;另一个,没了。
“这儿真冷啊,他们就是要冻死我。我心知肚明。”她说,口齿伶俐,眼神精明,说这些抱怨的话时底气很足,却并没有一丝愤怒,反倒有些大人不记小人过,又见怪不怪似的。一摸她的手,很温暖。我们早热得脱了外套。
“我啊?来这儿半年了,九月来的,这不嘛,现在是十月。”床头上贴着她的姓名、住址、病情、饮食状况等信息,住院时间一格是2007年2月,已经快三年了。
大诺站在床头,跟她唠起了嗑儿,俩人都熟面熟脸的样子,其实是头一次见面。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临了,她狡黠地歪着头打量着我们。
“姐弟!”
“姐儿俩?是嘛?”显然她并不信,眼里有了一抹笑意,随后便望着我们沉默了,那隐忍,明显释放出不屑,是不想拆穿你的克制。她当自己年轻时的精明从不曾远离。
另一张小床上半靠着墙纳鞋垫的年轻女护工来自甘肃,“这老太太,可厉害了,我每天给她擦身洗澡。她的东西我不能动,一动就拿拐棍梆我,嘿,打得可疼了。他有一个儿子,医院打电话,他都不肯来看她,除了通知说没钱了,才给打过来。没人来看她……”护工很憨厚地小声嘟囔。
有的房间是空的,四张床靠墙放着,被褥都在,人已经没了。床头柜上,摆放若暖壶,床下是塑料桶,除了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小小的房间空荡荡的,荒凉而又寂静。一幅观音菩萨卷轴画,述挂在窗旁的墙上,菩萨无声地望着这尘世间一隅。
各屋门口,都贴着烫金的字,某某大学“爱心小屋”,最多的一个门口有八张这样的金灿灿标签,也许是因为“甲流”,加之天冷,除了个别护理人员,我几乎没碰到一张年轻的脸。
“需要安静,心里明白不能交谈,请你握一握老人的手,给他一个微笑,老人会感到温暖……”另一张表格里,写着老人们的名字。
鸡皮鹤发,行动迟缓,表情呆痴。三层楼的各个房间,全是他们的世界。
这儿,就是让张大诺找到谈恋爱感觉的地方:北京东郊一所老年关怀医院。“去时很兴奋,回来时很高兴,这不是谈恋爱的感觉又是什么?”他微笑着告诉我。
大诺有句名言:这个时代有两类人值得关注,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先快乐起来的那些人,志愿者,就是后者!
张大诺,是我面对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