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趋势的几乎预测不到的结果之一(虽然单个的思想家,如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尔岑,当然还有尼采,对此已不止有模糊的概念),是道德激情与力量的品质以及浪漫的、艺术性的反叛的品质的降低。这种反叛曾是不满的社会群体在其早期的英雄时代进行斗争的标志,那时候虽然他们有深刻的分歧,但一起反抗暴君、牧师与武装的庸人。不管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公正与不幸是什么——它们很明显并不比刚刚过去的时代更少——它们现在已似乎无法在能言善辩的人物中找到表达。因为这种情绪似乎只能产生于整个社会阶级被压迫或被压制的时候。如马克思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时刻,这些被压迫群体中最有表达能力的、社会经济上最发达的领袖,被这种共同的情绪所鼓舞,暂时不仅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或环境说话,而是以所有被压迫者的名义说话;在那一时刻,他们的声音具有普遍的性质。
但是,社会的所有部分或几近所有部分已经或即将拥有权力这样一种形势,无论如何不利于那种真正无私的言辞。无私至少部分是因为满足还太遥远,因为原则只有在黑暗与空虚中才最清晰,因为这时内在的景象仍然能不受实际行动开始时必然会强加于它的混淆与蒙昧、妥协与外在世界的模糊轮廓的影响。任何一个体验到权力或者即将体验到权力的人,都不能够避免一定程度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就像化学反应,是由成长在旷野中的纯粹理想与它的某种无法预测的、很少与早先的希望与恐惧相一致的实现形式间的剧烈接触引起的。因此,要撇开后来的岁月,将我们带回到过去时代,仍然需要特殊的想象力。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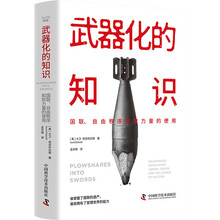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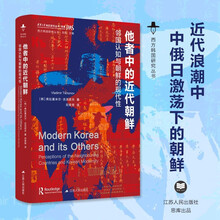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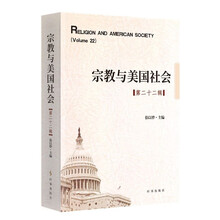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柏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
——罗纳德·德沃金
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
——约翰·罗尔斯
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
——查尔斯·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