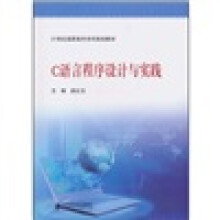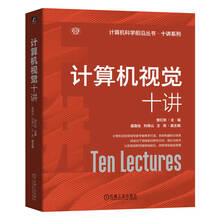买回一堆意义
我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再过十天就要回家了,这两天我开始四处转悠,想着给亲戚朋友买什么礼物。
昨天去了名品折扣店,一些过了季没卖出去的名牌,也就是名牌中的半老徐娘,在那里荟萃一堂。其实,我平时买东西,是最不讲究牌子的,觉得牌子这种东西,一是欺负人穷,二是欺负人傻,而我平生最痛恨被欺负。每次路过名牌店,我都侧目而过,很有点儿井水不犯河水的气概。
但是,给亲戚朋友买东西,总觉得还是应该讲究点儿品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没有追求,把什么都看透了。把什么都看透之后,就觉得人的很多追求,比如巨大的房子,比如巨大的戒指,除了心虚,什么都不是。再仔细想想,把什么都看透,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虚荣,还伤害了自己活下去的兴致。所以,附着在物质之上的很多“意义”,就像新娘头上的红盖头,还是不掀开来才好。
以前在国内读研时,和一个朋友合译过一本书,叫《礼物之流》,是一本人类学的书,大意是说:礼物这个东西,本质不是东西,而是“意义”,礼物的流动也就是“意义”的流动,秩序的流动,或者说得更严重一些,就是人类关系的流动。没有礼物,人类的生老病死这些事件,和动物的生老病死,也就没有了什么区别。
我一向觉得,人类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我的看法是,它就是一门从猴子的角度观察人类的学问。比如,作为一个人,对面有个人打着领带朝你走过来,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作为一个猴子,你看见好好一个人,脖子上绑一根绳子,绳子垂在胸前,神情肃穆地朝你走来,你肯定会觉得人类真幽默。你会想,人类为了装正经,连脖子上绑一根绳子这种事情都想得出来,还染上各种颜色和花纹,真是有两把刷子。
问题是你不是猴子,你得理解那根绳子上所飘荡的意义。
想到这一点,我就更觉得买一些“品牌”送人,是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因为我送给人家的,不仅仅是东西,而且是“意义”。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讲,一条地摊上买的围巾,和一条品牌围巾没啥大区别。但是,从“意义” 的角度讲,给“品牌”付款的那一刻,象征着我对你的重视,也就是你对我的“意义”。
于是,我就在这里转来转去,寻找价格适中的“意义”,这个“意义” 不能重到砸坏我的心脏,但也不能轻到让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意义”们前呼后拥,五颜六色,朝我挤眉弄眼,在它们的勾引下,最后,我买下了一大堆“意义”,其中包括五个钱包、两条围巾、一件衣服、两个挎包、三个装饰品、一双鞋。
后来,我气喘吁吁,买不动了,就坐在商场旁边的窗台上。我拿出纸和笔,统计我买了几样东西,还差几样。我算得很专心,勾勾叉叉打了满纸,脚边堆了一座小山似的礼物。
最后结账的时候,售货小姐笑嘻嘻地说:“你买了一大堆东西。”我真想纠正她,不是一大堆东西,是一大堆“意义”。我要把这堆“意义”装进箱子,坐上飞机,带回家,然后打开,一件一件拿出来,一件一件送到人家的手上,听人家的赞叹。到那个时候,我会想,所有这些无聊的牌子,无聊得多么有意义。
(摘自《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80后的高贵 回上海不久,因为一个很可笑的原因,把腰重重地磕了一下,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天,哪儿也去不成。这天终于下定决心,“忍痛”陪妻子去著名的浦江大道拍一点儿雨中夜景。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浦江大道离我家很远,一路上要倒两回地铁。所幸,已经过了下班的高峰期,一上地铁就找到了座位。
车行不久,便听到从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笛子声。可以说吹得很不专业,一听便知道,这一定又是某个残障人在车厢里假借奏乐唱歌行乞。这种情况在北京也常见。据说这些行乞者往往都是“有组织…‘受霸头控制”的,一天下来的收入比一般市民还要高许多。所以,一般人都不太会理会这些行乞者。我当时也没准备掏钱,但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生(大约有二十五六岁模样)从裤袋里掏出了两枚一元的硬币(上海市面上基本不流行一元的纸币)。我正琢磨着,这男孩难道真的会“糊涂”到看不透这些行乞者的花招?而且还要给他两枚硬币?笛声已经逼近,果然是两个残障者。吹笛的是个盲人,还有个像是智障的瘦弱女孩,一手领着他,一手拿着一个盛钱的旧饮料罐,在前边给他带路。果然如预料的那样,整个车厢都没人答理这两个行乞者,只有那个大男生把两枚硬币扔进了女孩手中的旧饮料罐中。不一会儿,那女孩领着盲人走过来,也把这旧饮料罐伸到了我的面前,我照惯例,只当没看见一般,他俩在我跟前待了几秒钟后,见我没动静,便无奈地向前走了。然后,一曲吹完,车厢里除了车子行驶发出的轰鸣声,就显得异常安静。我本以为这事就像以往所经历的那样,就此过去了。
因为行乞者不可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发出抗议。别人也不会再关心行乞者的“收益”,甚至都不会再多去看他们一眼。但突然间,就在那笛曲中止的一瞬间,那个大男生却冲着盲人离去的背影,鼓了几下掌。我一下愣住了。虽然车厢里照旧没有任何反应,所有人依然像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发生的事似的,保持着麻木的沉静和沉默,但我真的被震撼了。如果大男生只是给两元钱,表明他只是在施舍。但他用自己的掌声在表达他对弱者生存努力的一种声张和支持,他知道弱者在困境中除了需要一点儿钱币,更需要社会和人们在心理上的鼓舞和支持,需要大家把他们也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对他们任何一点儿生存努力,给予一点儿温暖的认同:我可以因为觉得这些行乞者的行乞可能是某种被把持的行业行为而不去理睬他们,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即便是被控制的、把持的,这些残障人本身也是绝对的弱者? 是的,社会中行骗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渐渐地在被骗中都害怕了、麻木了,对弱者渐渐失去了应有的那一点儿同情和哀怜。这次我在上海受伤,就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在小区后花园里锻炼,失手摔倒,腰重重磕在一块水泥棱子上,人倒地后有一两分钟完全不能动弹。过了一会儿,有个正在跑步的瘦小的老人经过我身边、,停了下来,问了声:“你怎么了?”他伸手把我拉起。我挣扎着起身,稍稍向周边一看,其实周边也有人在锻炼。但在这一两分钟里,他们都只当没看见,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拉我一把。
我不想责怪谁。也许这正是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我们必须控制住自己以往那种对乌托邦的虚幻寄托。
但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在必要时给弱者的生存努力一点儿鼓励呢?其实只是几下不需要什么成本的掌声而已,我们也许就能在我们生存的大环境里增添一丝必要的暖色。我想我首先要做的是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想不到给这两个身处困境中的残障者鼓一下掌?当然,当所有的人都不鼓掌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向着两个残障者鼓掌,这仍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