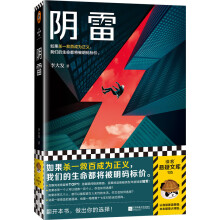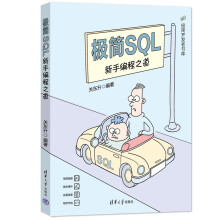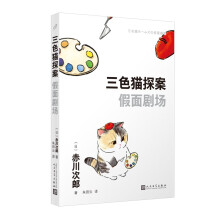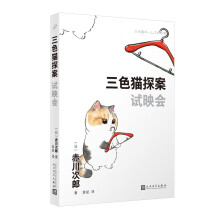鉴于瓦萨里希望用优雅来作为16世纪作品的特征,以便与15世纪的作品区分开来,他不能满足于这种不明确的表达。因此他采用了贝尼铁托·瓦尔奇在《书的美丽和优雅》(Librodellabeltaegrazia,1543)中的一句话--尽管他对这句话做了不小的改动。瓦萨里致力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优雅是否可以脱离美存在;另一个是美丽和优雅哪一个更重要。带着这个任务,瓦萨里灵巧地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放在一起比较。亚里士多德有着自然而实在的美,他四肢的比例协调且有悦目的颜色。如此,美确实是独立存在着的。而柏拉图类型的美,是精神上的美,包括人的美德。这种混有优雅的美和身体或物质都是无关的,而是从“能显示人物所有完美的外观”得来的。在人类中,这种代表物质的外在表现其实就是内心的袒露,因此“我们所说的优雅的美”,都是从人的精神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美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人们喜欢拥有这种美的人,就像柏拉图所说,这种人是“穿越并照亮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至高无上的美丽光辉”(在这点上,参见瓦尔奇于1535年的《爱的对话》中提到柏拉图的风格:“优雅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到喜悦的,让我们的灵魂充满爱的东西,是一种呼唤美的东西。”)。瓦萨里在区分意大利16世纪的美丽风格和15世纪的简单美时,没有用上面的例子,而是用瓦尔奇的观点来阐述,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也曾专门讨论过这个论题。
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c)的多样性,在《艺术家的生活》中有所展现。在书中,优雅的作用被加倍强调了。这是对“隐藏在艺术中的艺术”和那位廷臣的“正面消极”进行研究后的结果,也是个人技艺和极高天分的成果--让拉斐尔(他也是廷臣)能自如地将优雅体现在作品中,以此触动周围的人:对看画的人而言,一位优雅的画家往往能将这种优雅传递给画中的人物。在佛罗伦萨雕刻家德西德廖·达·赛蒂尼亚诺的传记中,这点已有所体现。他的作品体现了他“展现简约和优雅并为所有人所认可”的“天赐的才能”(瓦萨里写道:“这些作品中的天空和自然的元素使画作有着别的作品无法逾越的和模仿的优雅,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天分造就的。这些画作的优雅和魅力吸引着其他画家,甚至一些外行人。”),这个主题在《优雅的拉斐尔》中再次提及并被仔细讨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