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985-1952),20世纪“新弗洛伊德派”的代表。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的先驱。
1885年9月16日,霍妮出生于德国汉堡,受母亲影响颇深。1906年,21岁的霍妮考入柏林大学,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26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柏林“兰克维兹疗养院”研究三年的精神医学,追随德国著名神经学家赫曼·奥本海默学习。1915年,获柏林大学学士学位。
1915~1918年,霍妮任伯林精神医院住院医师,1920~1932年期间还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任教。1932年,霍妮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院长聘请,担任该院副院长。两年后,她迁居纽约,创办一所私人医院,并开始培训精神分析医生。随着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分歧的加大,她与研究所其他成员关系紧张。1941 年,她倡立精神分析改进会,并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亲任所长,直至去世(1952年)。
霍妮的主要著作有:《我们这一时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精神分析新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自我的挣指扎:神经官能症与人的成长》(1950)、《女性受虐狂问题》等。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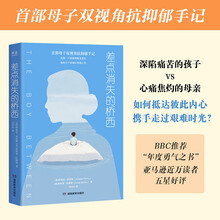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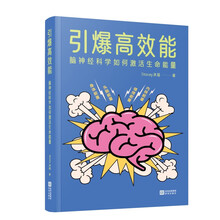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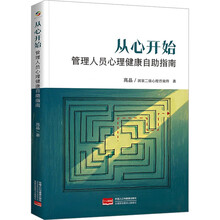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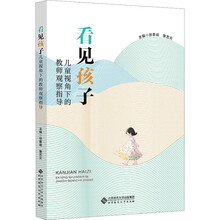



——奥本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