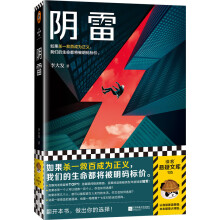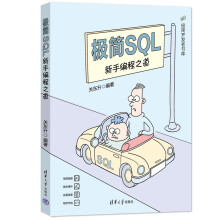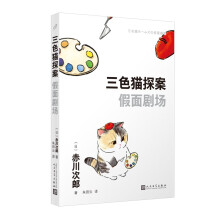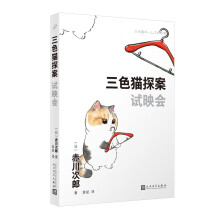此外,许多经济体都被名义上的“国家”公司所掌控,而实际上这些公司的生产、营销、运作和融资都是跨国性的。其结果就与以往大多数公司主要从本国境内开发资源、雇用工人、融通资金和打开市场的“国家”经济大不相同。
如同政府制度一样,各国经济结构的集中或分散度也有着重大差异。该经济体是否以高度个体化、市场驱动、较少中央协调和限制为标志?或者,是否存在超越短期市场定位的大规模的集中和协调?这种集中也差别巨大,比如,法国和德国最大的5家企业的营业额相当于其各自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数值则小得多,只有7%。
各国与市场的互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经合组织国家的公有和私有产权结构各不相同,它们在税收形式、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等方面也千差万别,其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研发开支、失业率、国家预算、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对幼稚产业和农业的保护以及公司投资也不尽相同。
这些多样性的核心差别就在于分割政治和经济领域或促使这两个领域融合与合作的制度安排的程度不同。少数国家,最明显的是美国和英国,长期试图通过限制政府机构的规范能力,将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传统机制化。像法国、日本等更多的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德国,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是经常的、紧密的、互惠的以及深层次的。
最后,有一套中间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利益集团协会、政党、政党体系和选举体系。它们在一国的社会经济特色和裂隙以及该国的统治制度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这方面的差别也非常大。在一个极端,社会集团可以自由组建、自由筹款、自由选择其活动,而不受政府的领导、监管和控制;在另一个极端,这些集团的生存依赖于某些政府机构给予它们的地位、资金和监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