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
罗伯特?福格尔
到204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全球经济总产出的三倍。到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000美元,预计将比2040年的欧盟人均收入多一倍,同时也将大大高于印度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换句话说就是,当中国从2000年的贫穷国家发展成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时,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将过上比普通法国人好两倍的日子。尽管在人均财富上的排名它还不会取代美国,但据我预测,30年后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将达到40%,这将使美国(14%)、欧盟(5%)相形见绌。这就是一个经济霸权未来的样子。
目前绝大多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报告不仅很少提到这一点,甚至还经常有些含糊不清或危言耸听的空泛言论。同时它们往往极大地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的程度和增长速度。(举例来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会比美国大20%。)这种报告未能全面地肯定中国近年来一系列成就背后所酝酿的力量,也没能了解这个趋势对塑造中国未来将起到怎样的作用。甚至中国自己的一些经济数据在某些方面也低估了实际的经济产出。
与此同时,受低生育率影响,欧洲作为全球经济动力的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将结束,而面临相对衰退。同样,经济曲线将比大多数报告所表达的还要更为突兀。欧洲的低出生率和它消退的消费主义意味着,在30年后,它对全球GDP的贡献将跌至现有份额的四分之一。如果是这样,那么欧盟最早的15个初始会员国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将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八分之一。
这就是未来一代人将看到的变化,它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要快。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中国变得如此成功?
最初的基本因素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中国在教育上的巨大投入。受教育越多的工人就是更具有生产力的工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讲的,美国的数据表明,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工人相比,大学毕业的工人的生产力水平是其3倍,高中文化的工人的生产力水平是其1.8倍。)在中国,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在政府的加大教育投资的政策推动下急剧增长。1998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号召高等教育要扩大招生。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响应。当年中国高校的在校生仅为340万人,四年后,高校在校生增加了165%,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加了152%。在2000年到2004年间,高校人数继续急剧增长了约50%。我预计中国将用下一代人的时间,把高中人数再扩大100%左右,高校则再扩招50%。这样,这些自身的努力将使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增加6个百分点以上。这些提高高等教育率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你一定还记得,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几个西欧国家的高校入学率出现了25%~50%的增长。
而且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体因教育程度的增加,劳动力得到显著地提高,根据经济学家埃德温?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在他197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著中,曼斯菲尔德指出,相比于对革新反应比较迟钝的企业老总,那些能够快速采用复杂新技术的企业总裁的平均年龄都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许多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低估的第二个原因是,忽视了农村因素带来的作用。当我们设想未来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描绘上海的摩天大楼和广东大片的工厂,而忽视了正在变革中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未被估量的经济引擎。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时,我们常常将经济划分为三个产业部分:农业、服务业、工业。在1978年到2003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间,中国每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大大地提高了,年均增长6%。尤其是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人人均产出水平要更高一些。也正因为此,这些产业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和分析。(我估计中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然而,即使在仍是农村的地区,生产力也在增长。2009年,约55%的中国人口,即7亿人,仍然居住在农村。这巨大的农村部分承担着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责任,而且在未来三十年里它也不会消失。
第三,尽管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在一些关键部分都掺杂了水分,但中国的统计部门也还是有可能低估了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在服务业确实存在,因为小企业常常对政府瞒报数据,而官方也往往不能有效地对生产在质量改进和产出上做出足够的评估。在美国也存在一样的情况。如果政府没有把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的改善纳入统计数据中,那么官方对GDP增长的预测就会大大低估。(这些领域的重大进步没有被充分地计入GDP中,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估价是以投入而不是以产出来衡量的。与抗生素和现代外科手术出现前的时代相比,今天一个医生一小时的价值被认为已经缩水了。)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国民经济核算问题,但中国服务业的飞速增长速度使这个低估的问题变得更为明显。
第四,也是令一些人最感惊讶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尽管外界的观察者总是假定北京始终是掌舵者,但是大多数的经济改革,包括最成功的那些例子,都是由地方政府实施和监督的。当然,中国不是开放的民主制国家,但在高层决策中的批评与辩论要比许多人认识到的要多得多。未经检验的行政命令当然会导致灾难,因此近些年来北京一直努力避免重复“大跃进”的错误。
举例来说,中国经济学家协会的年会每年都会举行,我也曾多次参加。有些与会学者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尖锐的抨击——而且非常公开。当然,他们不会说“打倒某某某”, 但他们会指出财政部最近做出的决策是有问题的,或是对提高电和煤的价格表示忧虑,或是呼吁关注股权发行。他们甚至可以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批评文章。然后中国的财政部长可能就会真的打电话给他们:“你能不能叫上一些你们的人?我们好派些人与你们见面,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你们的想法。”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发生在北京的这种你来我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过去相比,中国在经济规划上对新的观念更加开放和积极响应了。
最后一点,人们对中国长期受抑制的消费主义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中国是当今世界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例如与捷克相比,就已经高出那里的生活水平了。在这些大城市里,一些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尽管中国人有特别偏好储蓄的习惯,但对服装、家电、快餐、汽车等需求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未来。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判断,即增强国内需求对中国经济将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中国国内许多政策都是旨在刺激消费,提高中国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那么欧洲又如何呢?我指的是15个欧盟初始会员国的欧洲,面临着人口问题和文化的双重挑战,它的经济前景受制于生育习惯和消费抑制的双重桎梏。
当然,到2040年欧洲人也不会吃草度日。他们未来三十年的经济衰退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欧洲的总体劳动生产力将会以每年1.8%的速度持续增长。不过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他们对全球GDP贡献的百分比会下跌,降到原先的四分之一,即从21%跌到5%。
人口问题是欧洲最核心的问题。西欧的人口一直在迅速老龄化,而且这种老龄化的状况很可能还会一直延续几十年。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的夫妇不能生育足够的孩子。根据2005年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34年来欧洲人口总体出生率一直在更新人口的需求水平之下。其结果就是,在生育年龄内的妇女比重将会下降。据联合国预测,在欧盟的15个初始成员国中,育龄妇女在妇女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约50%(1950年也是50%),将跌至2040年的35%。这样就给了我们双重打击:不仅育龄妇女会急剧地降低生育率,而且育龄妇女的比重也会急剧减少。到2040年,几乎三分之一的西欧人口将超过65岁,步入花甲之年。
为什么新生儿会越来越少呢?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欧洲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百五十年前,享受性爱被认为是有罪的,性生活唯一合乎正道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而在今天,年轻女性们认为性爱主要是一种娱乐活动。在生育率变化的背后,是文化的巨大转折,转折点正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还是早婚,并在1945年到1965年间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期。然而,随后的便捷的节育手段和享受性爱思想的滋长,意味着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将会下降。早在2000年,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减去死亡)就已经是负值。到2040年,除了英国,欧洲五个最大的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可能都会是负值。
那么欧洲人偶尔享乐一下又会如何呢?当然享乐是有前因后果的。出生率下降推高了公民的年龄,缩减了从事劳动的人的比例,从而妨碍了经济增长。人口构成的改变也将影响私人企业的雇佣和提升结构,而这并不一定是向着好的一面转变。如果老人们过了退休年龄还把持着肥缺,那么年轻职员就得多等上十年,或更长时间,然后才能轮到他们。由于年轻职员是新观念的主要来源,因此延迟新一代的上台就可能妨碍技术革新的步伐。(如果出生率一直保持这么低,意大利的人口在50年之后就会减少一半。当然,政治家们已经在尽其所能。他们和教宗组织一道,劝诫适龄女子:请生儿育女吧。)
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使经济学家们无可奈何。欧洲富国的公民们不喜欢多劳多得。相反,欧洲文化一直是宁愿鼓励长假、提早退休、减少每周工作时间,也不愿通过加班获得更多的物质奖励。至少,比起像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是这样。据我的观察,比起美国人,生活在西欧国家的人更容易满足于已获得的商品。比如说,每个家庭并不追求多摆几台电视机。且不论是对是错。宁愿去卢森堡公园散步也不愿去沃尔玛买一台纯平电视,这对欧盟的GDP增长不会有任何帮助。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要面对的麻烦。怀疑论者指出诸多可能在未来30年导致快速飞驰的中国火车出轨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领土争端、燃料匮乏、缺水、环境污染,还有依然脆弱的银行体系。尽管批评家们说得有些道理,但他们的这些担忧中国领导人知道得很清楚。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对解决问题对症下药已经越来越专业。除此之外,对中国来说,历史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台湾主权这个争议最为激烈的地区问题上,现在似乎也向着可解决的方向发展。在国内,结合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公众意见的敏感度也在不断提升,从而使大众对政府形成了一种广泛的信任。因此,依我的观点,中国不可能出现大的政治动荡事件。
欧洲是否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其可持续增长率比我预测的高?这看起来有些牵强。但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既要靠欧洲人削减假期和午睡,赋予工作更多的热情,也要靠更多的年轻女性和她们伴侣的性爱观念更偏向宗教,而不是电影明星。一切皆有可能,但也别过于指望它——欧洲人似乎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好,而且他们也早已放弃了称霸世界的梦想。一场意想不到的技术革命也许会让事情有所转机,然而这种事情就不是经济学家们进行预测时所能采用的了。
对于西方人来说,全球经济重心落在亚洲的观念可能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但这种现象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正如中国学者常常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间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是他们对历史做了漫长的回顾后得出的结论。(彭定康,最后一个英国港督,认为在过去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当欧洲还在中世纪早期的黑暗中摸索,在灾难性的宗教战争中搏杀时,中国却发展成为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今天,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崛起的观念,只不过是回归历史正途。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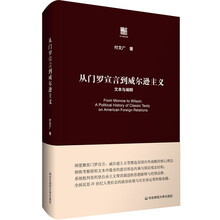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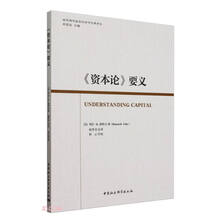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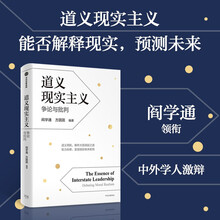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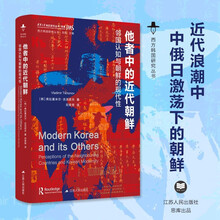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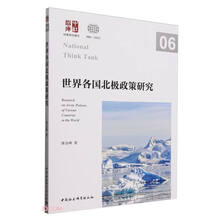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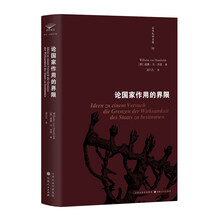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特邀国内外17位知名学者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把脉,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贸易、农业等方面,为我们勾画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致轮廓,以及应该关注的问题。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出一个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必须关注的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中国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和定位直接相关,其他国家必须关注这个问题则是因为中国对全球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下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转变,2049年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评估近年来的趋势,如何应对当前和即将出现的挑战。我们希望听取不同国家各方人士的意见,使本书成为广泛辩论的基础。我们希望它能够对所有期望理解和塑造我们共同目标的人们有所助益。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发更多的挑战,获取更多的建议,以处理那些塑造中国未来和世界未来的挑战。中国未来面临的趋势和挑战艰巨而复杂,将影响整个世界,没有各国专家的才智,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