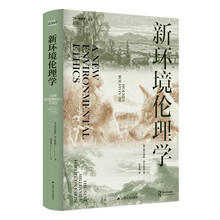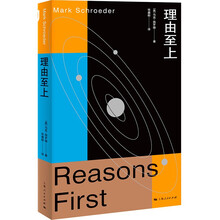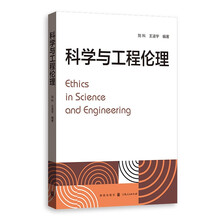避公众的检查和批评。科技已成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因为它是创造利润和管理控制的无可争辩的关键之一。
总之,科技参与了以上所说的伦理转变的三个现代过程,即取代、淡漠化和殖民化。科技实践不仅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取代了伦理学,而且对从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驱逐伦理发挥了作用。规范合理性被认为是与工具主义要求不相容的,被认为是与技术上有用的客观知识内在冲突的,于是被限制在私人领域。科技把非道德性提升为一个新的社会性原则,一个彻底限制了我们对社会建制之作用的理解的原则。国家和市场变成了严格的解决问题的组织,其结构则服从于控制、效率和功利的要求。人们认为,它们不过就是不同利益(冲突)的中立裁决者,它们通过配置资源和对偶发危机提供技术解决而管理着现存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使社会的自我建制以及公民的规范性自决得以重塑?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回答另外两个问题。如何填充科技在其自身活动范围和更广泛的社会范围所造成的伦理真空?如何克服与此相关的民主失误?能支持公民自主性的科技的伦理化和民主化是不能分别考虑的。仅当科技被置于公共领域的振动之中,即科技的可接近性、责任和义务能得到讨论时,它才可能被伦理化。另一方面,科技的民主化又依赖于一个能使时代的重大社会和伦理主题得到认真审视的公共空间的存在。
为把科学技术重新放置于公共领域,既要通过规范性的生活世界把科技领域的殖民化颠倒过来,又要用实质性的、价值导向的和出于公心的行动和思维方式去抵制官僚化和商品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着手抵制取代、淡漠化和殖民化,从而把科技置于“伦理化”和民主化的社会一文化体制中,这样的体制是充满伦理关怀的,是服务于公共善的,同时又是受全体公民控制的。首先,科技必须根植于公共领域,这公共领域是就科研一般方向、具体技术发展后果以及两者的伦理标志进行讨论、争论和慎思的竞技场,人人都可参与这样的竞技场。所以,公共性要求科学成为充分可接近的,是可以被公民们所审视的,且最终是对公民负责的。关于科学发现之方向、意义和应用的重大决定不能只留给专家们,无论他们是政治家、军事领导人、公司经理,还是科学家。科技的最终主权必须归于公共领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