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的发生是自发的,其包含也是自发的;相对于人的认知,其包含是前在的,不是后生的。而且认知也不能穷尽it,it永远大于对it的认知。It的完备性同时蕴含了它的特异性、单一性。因为是在特定时间情境中发生的,因为具有巨大的完备性、内涵饱满、充满活力,it就去掉了一般性、平庸性,成了不可替代的状态。就其作为人生的现象而言,它意味着这一刻发生的事永远都属于这一刻,永远不可重来。它不代替过去,也不代替未来,它就是它自身,也只是它自身。所谓“只是自身”、“不可重来”,不意味着人生只能生活在某个不可重来的时刻。历史上是有人将自我的人生固置在某个不可重来的时刻的。古代中国沉湎于伤逝情怀的诗人就是如此。“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元稹这首广为人知的绝句言说的就是伤逝情怀。它表明,诗人的生命固置在和已逝恋人相连的过去的生活情形之中。It的不可重来之所以不导致人生在不可重来的过去情形中的固置,根本原因在于:“it”不等于“人生”。人生是由it构成的。构成性“要素”不能取代被构成的整体。It的特异性和单一性包含了在时间中it对自身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一个特定的it消失,让位于接踵而来的it。人生就处在由无限多样的it构成的过程之中。让某一个特定的it凝固、恒定,取代整体性的人生,这实际上是取消it的单一性和特异性。从人生哲学上看,中国古代的伤逝文人就陷入了这样的盲区。现代有学者热衷推崇这种极具传统中国特色的伤逝哲学,①说明他们哲学思维方式陈旧。当代中国日益高涨的文化复古情绪实际上也包含着同样的浅陋。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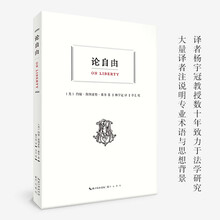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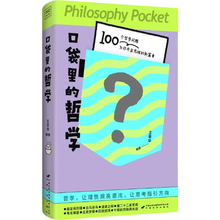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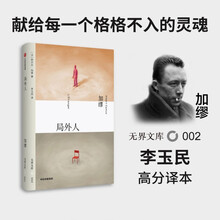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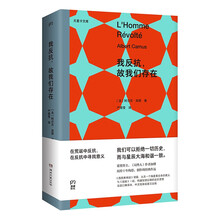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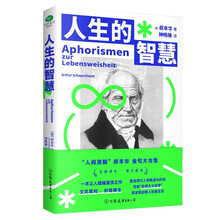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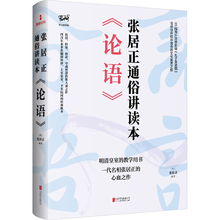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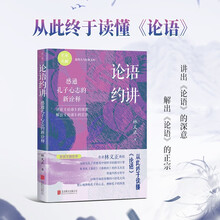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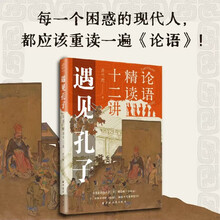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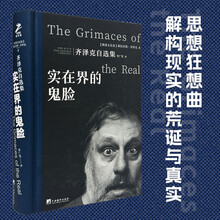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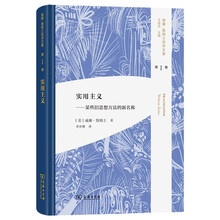
——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