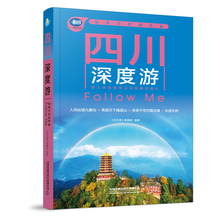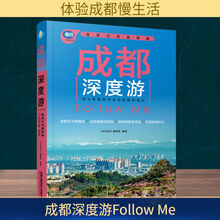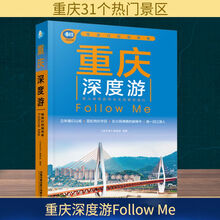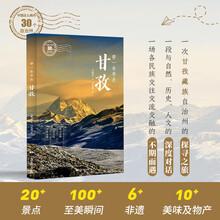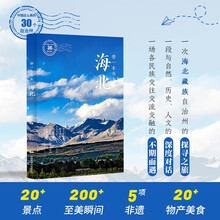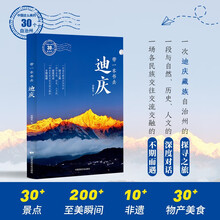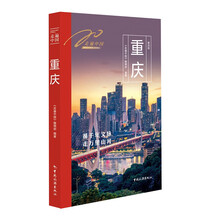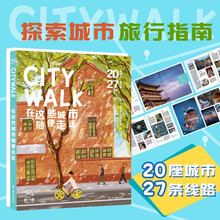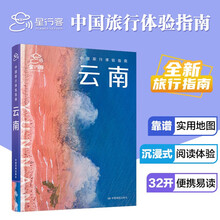解读新疆,深度行走。
新疆是一个童话,在这里,人类最初的某些记忆得到了完整的保存,由此人们希望重返新疆时得到提升,留下回忆,获得解脱;新疆是一个通道,从这里进入,世界的全部细节仿佛如莲花般打开,一切疑问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新疆是一种痕迹,本能地记载着一些关系。
后记
在我的新疆 并不遥远的1957年,我的父母从甘肃天水甘谷县大石乡一个名叫丁家坑窝的村子出发,坐着毛驴车、火车、卡车、木板车……来到了新疆哈密,在一片名为“花果山”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自己打土坯,盖起了两间土屋,在门前栽下了白杨树,在屋后的田野里种上了白菜和辣椒。菜地被一片河滩阻隔,河滩背后是一片邻村的麦地。这片河滩有大小两条河流,长满了柳树,被称作“左公柳”,是左宗棠部队在哈密时留下的。
1971年秋天,我出生在土屋中,一切都波澜不惊。那时,父母从维吾尔族邻居家“请”来的葡萄枝已长大成树,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凉棚,那些葡萄藤枝繁叶茂地爬了上去,将一串串果实垂挂下来。两岁时,我记得自己穿着一双绿色的毛线小鞋,跑在宽大的炕上,一抬眼,看到了窗外的绿树就用手指着说“葡萄”。
1993年之后,我定居在乌鲁木齐。因T作之便,走遍了新疆的所有县、市。这种跨越天山南北的旅行常常会催生我写作的欲望,而我几乎所有的写作题材皆取材于新疆大地。
我试图用文字挽留住一种记忆。无论是诗歌或者小说,或是散文随笔,都是一种对记忆的挽留。它们之间并不能相互取代,而往往在诗歌和小说的想象之翼展开之时,还需要人文随笔中那些坚实的历史、地理知识作为支撑。如果我们总是迷恋飞翔,那天空就会显得过于空洞:如果我们总在大地上行走,就无法让自己飞身出来,达到更高的境界。
2006年,我重走新疆大地之后,写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文字。此前,我对新疆的描绘是艺术的、片断的、细节的,还没有如此“完整”、“准确 ”、“恢宏”地描绘过新疆。面对新疆大地,我的写作像窗外的冬日,变得越来越沉重。我手中的笔仿佛灌了铅,愈发艰难起来。如何能写好新疆? 如果我是一个单纯的旅行者,我会原谅自己对现在的疏忽,我会马上找到下一个目的地;而新疆,却是我的家园,是我不离不弃的爱人,这让我在表达的时候越发艰涩起来。
新疆是一个童话,在这里,人类最初的某些记忆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南此人们希望在重返新疆时得到提升,留下回忆,获得解脱;新疆是一个通道,从这里进入,世界的全部细节仿佛如莲花般打开,一切疑问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新疆是一种痕迹,本能地记载着一些关糸。那些千佛洞中的壁画是脆弱的、容易毁灭的,那些雕刻在石头上的岩画却又是经得起千年万年风吹日晒的。看看那些披红挂彩的飞天和手拿长矛的原始人,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多大差别? 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去喀什香妃墓时路过一个大涝坝,旁边有几户人家,一位穿着白衣戴着花帽的老人坐在土炕上,模样很像我的老父亲。我拿起相机时,却从镜头里看到他朝我摆摆手,将头扭到了一边。
我的脸像被烙铁烫着般,阵阵泛红。
作为一个窥视者,我侵犯了他的生活——他完整的生活在我目光的掠夺中变得残缺。当新疆面对太多的镜头时,新疆被切割,被分离,被取样。每个人通过他的镜头看到了“他的新疆”。他看不见的那部分,就被忽略不计了。如果照相机或者摄像机所建立的图像世界是携带着“取景框” 的话,那么文字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在我所堆砌的这些文字背后,那些景点和景点之间漫长的距离,那些景点之外被遗漏的美和忧伤,都将因没有记录而显得“空空荡荡”吗?而这种没有被窥视和记录,对于它们来说,到底是一种不幸还是万幸? 在和田的巴扎上,那些卖一只鸡或一把奥斯曼的老人都沉默不语。他们绝不叫卖。他们慢慢地等待,并享受这种“慢慢地等待”……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被消磨过去,但我的内心却一直被一种危机所笼罩。最后的…… 最后的……这些最后的坚守,是我所敬畏的。可是,那些缓慢的速度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了。已经有很多人抱怨说:骑马时牧人要收钱!住宿时农户要收钱!我总感到我们的旅行似乎在伤害着新疆,惊动着新疆。如果没有旅行者,没有所谓的景点,也就没有这些抱怨:可是,凭什么新疆的牧人和农户要傻乎乎地等待着“你”的廉价窥视呢? 如果我们热爱旅行,如果我们试图从更边缘的人们的生活巾找到自己生活的支点,那就不要带着一种优越感进入新疆。多少次,我看见那些装备精良的旅行者大踏步地进入新疆,爬上某座雪山或者漂流过某条河流,在某个小村庄前摆个“POSE”,我总在想:新疆的魅力,决不仅仅在于风景,更在于那些民俗民情……如果有足够的耐心,让我们看看那些白发老人的眼睛,看看躺在木质摇床上婴孩的眼睛,看看玫瑰花丛中姑娘的眼睛 ……新疆的魅力,就藏在这些眼睛背后。
最后,让我说声“感谢”: 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蔡安编辑“牵线搭桥”,本书编辑江丽芝“精心哺育”,才让这本书从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现实。
本书部分图片由“葡萄摄影专家”龙建强先生、著名民俗摄影家韩连资先生、博州温泉旅游局张帆先生、乌鲁木齐美女红袖女士、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族诗人艾尼瓦尔先生提供,待此感谢。
本书地图初稿由宋志宏先生绘制,他还担任了本书的第一校对,对他所承担的具体而琐碎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宋丁丁小朋友,因为他的好胃口、好身体、好心情,让我得以腾出时间来伏案写作。
感谢诗人安歌,感谢作家骆娟、诗人兼画家毕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具体指导,共同陪伴我度过最艰难的写作阶段。
感谢所有关注我的老师、朋友、网友,你们的注目是我身后最坚强的支柱! 让我们自由自在,让我们身随心动。
让我们在享受阳光和大地的同时,感恩生命。
丁燕 2007年1月29日于乌鲁木齐葡萄山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