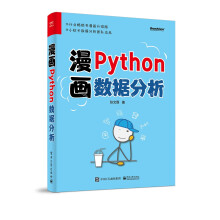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龟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br>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子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语)暴露无遗,我们只好承认,国家嘛,还是交给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员的事情——这些按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当然是西方的定义),本来就水是咱们知识分子的事。咱们知识分子,观近代国学大师可知,其职任端在“人文关怀”。尽管这样的考虑已接近变局的谷底,比起前一类幻想似较为务实,但听起来却有点像是“临终关怀”。 ……
展开